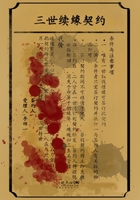第7章 种麦子(一)
亲王府的北魏孝武皇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秋霜染白了田野最后的生机,也催动着冬小麦播种的时节。在吴普同家那六亩薄田的规划里,两亩留给来年的棉花,两亩给不可或缺的红薯,半亩用来点种金贵的花生,而剩下的土地,则毫无悬念地要奉献给冬小麦——这维系着全家一年口粮与希望的根基。 不同于后世精耕细作的繁复,那时的麦种,朴素得近乎原始。没有包装袋上印着高产抗病字样的商品种子,更没有花花绿绿的拌种剂。种子的来源,就是去年自家麦收时,特意挑选出来、颗粒饱满的那部分。母亲李秀云在夏日的某个阴凉午后,坐在堂屋门口,用一个圆形的簸箕,将麦粒一遍遍地扬起来。金黄的麦粒在空中划出小小的弧线,借助风力,那些干瘪的、不够分量的秕粒和夹杂的草屑、土坷垃便被分离出去,落在远处。剩下的,便是沉甸甸、黄澄澄、带着自家土地气息的麦种。它们被小心地装进布袋,挂在仓房通风干燥的梁上,等待着秋播的号角。 播种的工具,也带着浓厚的自力更生色彩。吴建军在农闲时,早已准备好了播种的家伙什。工具的核心,是两根粗壮结实、呈“人”字形分叉的硬木树杈(通常是枣木或槐木)。他将两根树杈的“腿”并拢,用粗大的铁钉牢牢地钉死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固的倒“v”字形框架。在“v”字底部交叉点向后延伸出去一截木棍,斜斜地指向地面,这根延伸的木棍末端,被巧妙地安装上了一个闪烁着冷光的、尖锐的铁质犁铧头。整个工具,看起来像一个结构简单却异常坚固的、拖着“尾巴”的木犁。 播种的日子,选在一个晴朗微寒的清晨。天空是那种洗练的湛蓝,几缕薄云像扯散的棉絮。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干草混合的清冷气息。吴普同早早被叫醒,他知道今天是个“大日子”,不用去幼儿园,可以全程跟着去地里。 父亲吴建军和母亲李秀云合力将那个自制的木犁抬到板车上,又把几大袋沉甸甸的麦种搬上去。吴普同兴奋地爬上车,坐在麦袋旁边。板车在父亲沉稳的拉动下,吱吱呀呀地碾过村道,驶向预留的麦田。 田野里,已有不少人家在忙碌。相似的木犁,相似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充满原始劳作美感的秋播图景。 到了地头,吴建军卸下工具。他拿起木犁,将带着锋利犁铧的“尾巴”插入干燥的土壤中。母亲李秀云则熟练地将一根粗麻绳系在木犁前端的横档上,然后将绳子的另一端,斜挎在自己坚实的肩膀上。 “来,同同,你站远点看,别让犁头碰着。”父亲叮嘱道。 吴普同乖乖地退到田埂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只见母亲李秀云身体微微前倾,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声:“走嘞!”她肩膀发力,拉动麻绳,身体像一张绷紧的弓,开始向前迈步。与此同时,站在木犁后面的父亲吴建军,双手紧握木犁后部延伸出来的扶手,也同时发力向前推!夫妻俩的步调必须高度一致,力量要协调。 “嗨——哟!”随着一声低沉有力的号子,那尖锐的铁犁铧在两人合力的驱动下,轻松地破开了干燥坚实的土地,划出一道笔直、深约两三寸、宽约一掌的沟槽!被犁开的湿润黑土像波浪一样翻卷到沟槽的两侧。泥土被撕裂的“沙沙”声清晰可闻。 就在犁铧破土前行、沟槽形成的瞬间,站在沟槽旁边的父亲吴建军,空出一只手(这需要极强的平衡和控制力),极其精准地从挎在腰间的布袋里,抓出一把金黄的麦粒!他的手臂随着前进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挥洒,麦粒如同金色的雨点,均匀地、簌簌地落进那新开的、湿润的泥土沟槽里! 一步,一沟,一把麦粒。母亲的肩膀承载着向前的拉力,父亲的双手掌控着犁沟的深度、方向和撒种的精准。他们的动作流畅而富有韵律,像一首无声的土地赞歌。汗水很快浸湿了母亲的鬓角,父亲额头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们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所有的力量和精神都凝聚在脚下新开的沟槽和手中播撒的种子上。 吴普同看得入了迷。那简单的木犁,在父母默契的配合下,仿佛拥有了生命。它不再是粗糙的木棍和铁块,而是连接大地与希望的桥梁。看着金黄的麦粒消失在黝黑的土壤里,他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播种”这个词所蕴含的庄重与期待。 一垄地开完、种完,父母会停下来稍作喘息,喝口水。然后,吴建军会调整木犁的位置,紧挨着刚刚播种完的那一垄,再次将犁铧插入土壤边缘。母亲再次拉动绳索,父亲再次推犁、撒种……如此循环往复,一垄接着一垄。金色的种子,就这样随着他们沉重的脚步和辛劳的汗水,被深深地埋入滋养它们的土地。 当一片区域播种完毕,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覆土盖种。这时,吴普同最期待的环节来了。 工具是一个长方形的、用细竹篾或荆条编成的“盖”(类似一个巨大的、没有边框的竹帘子,也叫“耢”或“盖耙”)。父亲吴建军在“盖”上压上几块沉重的土坯或石头,增加重量。 “同同,上来!”父亲招呼道。 吴普同欢呼一声,手脚并用地爬上那个巨大的竹盖,一屁股坐在压着的土坯旁边。他的重量虽然不大,但也是重要的“压舱石”。 父亲吴建军走到“盖”的前端,将一根粗绳套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像拉犁一样。母亲李秀云则站在“盖”的两侧或后面,双手扶着竹盖的边缘,控制方向并施加向下的压力。 “坐稳喽!”父亲一声吆喝,肩膀猛地发力,拉动绳索。沉重的竹盖被拖动,开始在刚刚播种过的土地上缓缓移动。吴普同坐在上面,感觉像坐上了一辆奇特的土橇车。竹盖碾过松软的、带着新鲜犁沟痕迹的土地,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它粗糙的底面,将翻卷在沟槽两侧的湿润泥土,轻柔而均匀地推回、覆盖在撒了麦种的沟槽上! 颠簸!这是吴普同最直接的感受。土地并不平坦,竹盖在父亲的拉动下,随着地面的起伏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吴普同的小屁股被颠得有些发麻,但他紧紧抓住竹盖的边缘,非但不觉得难受,反而觉得无比新奇有趣,咯咯地笑出声来。他感觉自己像个小小的国王,巡视着他刚刚被“种下”的土地。他低头看着竹盖滑过的地方,那些新开的沟槽不见了,麦粒被松软的泥土严严实实地盖住,地面变得平整而细腻,只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竹盖拖过的痕迹。 “盖”在田里来回走了两趟,确保所有播下的麦种都被土壤温柔地拥抱、覆盖。吴普同的“压盖”工作才告一段落。他意犹未尽地从竹盖上爬下来,蹲在田垄边,好奇地扒开一小块刚盖好的土,果然看到几颗金黄的麦粒静静地躺在湿润温暖的土壤里,像沉睡的婴儿。 太阳渐渐移过头顶,又从西边斜斜地照射下来。父母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上不断重复着拉犁、撒种、覆盖的动作。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泥土沾满了他们的裤腿和布鞋。吴普同有时在田埂上追逐偶尔飞过的蚂蚱,有时帮父母递水壶,更多的时候,是静静地坐在田埂上,看着父母沉默而坚韧的背影,看着那简陋的木犁在土地上刻下生命的痕迹,看着金色的希望被一捧捧泥土掩埋。 当夕阳将天边染成橘红,最后一把麦粒也终于撒入了泥土,最后一片新播的土地也被竹盖平整地覆盖好。六亩地里属于小麦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这场古老而神圣的播种仪式。新翻的泥土在夕阳下泛着湿润的油光,散发着独特的芬芳。疲惫不堪的父母,看着这片被他们亲手梳理过、播下希望的土地,眼中流露出的是如释重负的平静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冀。吴普同的小手也沾满了泥土,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抓起一把带着麦种余温的泥土,紧紧攥在手心,仿佛也攥住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对来年麦浪的朦胧憧憬。暮色四合,一家三口拉着空了的板车和农具,在归巢鸟雀的鸣叫声中,踏上了回家的路。田野归于寂静,只有新播的麦种,在黑暗温暖的土壤深处,悄然萌动着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