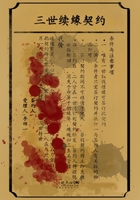第18章 回姥姥家
亲王府的北魏孝武皇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正月初二,回娘家的日子。西里村通往小李庄的土路上,积雪被来往的脚印踩得瓷实溜滑,在清冷的晨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李秀云挎着一个沉甸甸的柳条篮子,上面盖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印花布。篮子里装着年前特意留下的好东西:一包雪白的炸油条(用珍贵的白面炸的)、一包金灿灿的炸年糕、还有一小包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吴建军留在家里看门,顺便招待可能来拜年的本家亲戚。李秀云则带着三个穿戴整齐的孩子——穿着绿“军装”一脸期待的吴普同、穿着红底白花罩衫蹦蹦跳跳的小梅、以及被裹成圆球抱在怀里的家宝,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三里来路,在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兴奋和脚下咯吱咯吱的雪声中,似乎缩短了不少。吴普同不时回头看看母亲挎着的篮子,想象着里面的美味,脚步也格外轻快。空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硝烟味,但更多的是田野清冽的气息和对姥姥家温暖的向往。 抵达:暖炉边的亲情 远远看到小李庄熟悉的轮廓,李秀云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几分。刚走到村口那棵标志性的老榆树下,就看见姥姥家低矮的土坯院门敞开着,门口扫得干干净净。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袄、头发花白、腰身微佝的身影正倚着门框张望——正是姥姥! “娘!”李秀云远远地喊了一声,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姥姥!”吴普同和小梅也像撒欢的小马驹,挣脱母亲的手,飞奔过去。 “哎!我的秀云回来啦!同同,小梅!快让姥姥看看!”姥姥布满皱纹的脸上瞬间绽开了菊花般的笑容,张开双臂,把扑过来的两个外孙紧紧搂在怀里,粗糙温暖的手掌摩挲着孩子们冻得冰凉的小脸。“哎哟,都长高了!穿新衣裳了!真俊!”她接过李秀云怀里咿咿呀呀的家宝,在他粉嫩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家宝也来了,姥姥的心肝儿!” 院子里,听到动静的舅舅李建国(李秀云的哥哥)和大姨李秀英(李秀云的大姐)也迎了出来。舅舅身材高大,脸庞黝黑,是典型的庄稼汉子,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秀云回来啦!快进屋,屋里暖和!”大姨则显得更朴实些,脸上带着常年劳作的痕迹,但笑容同样热情:“路上冻坏了吧快上炕暖和暖和!” 二姨李秀芬(李秀云的二姐)和二姨夫赵志刚(在镇上粮站工作)还没到。堂屋里,一个用砖头和黄泥砌成的火炉烧得正旺,炉子上坐着一个大铁壶,壶嘴“滋滋”地冒着白气。屋里暖烘烘的,弥漫着柴火燃烧的暖香和一种混合着老人气息、食物味道的独特“姥姥家味道”。炕也烧得热乎乎的。 团聚:喧闹与温情 一大家子人挤在温暖的小屋里,瞬间热闹起来。 孩子们的天堂: 吴普同和小梅立刻成了中心。舅舅家的大表哥李强(14岁)、二表哥李壮(12岁),大姨家的表姐大丫(10岁)、表弟石头(8岁),都围了上来。孩子们虽然平时见面不多,但血缘的亲近和新年的兴奋让他们瞬间熟络起来。李强拿出自己做的木头手枪炫耀,李壮则显摆他捡到的几个特大号炮仗。小梅很快和大丫玩起了翻花绳。家宝则成了姥姥和两个姨的“掌中宝”,被轮流抱着逗弄。屋里充满了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嬉笑声、告状声和兴奋的叫嚷。 大人们的“唠嗑”: 李秀云、大姨李秀英、舅舅李建国围着火炉坐下。李秀云把带来的篮子递给姥姥:“娘,带了点油条和年糕,您尝尝。”姥姥嗔怪道:“回来就好,带啥东西!家里啥都有!”话虽这么说,但脸上是藏不住的高兴。 话题很快扯开了。 收成与生计: 舅舅抽着旱烟,说着去年的收成和今年的打算:“麦子还行,就是秋苞米让那场雹子砸得不轻……开春得想法子多弄点化肥,不然影响产量。” 家长里短: 大姨说着自家的事:“大丫开春该上三年级了,石头也淘气,整天上房揭瓦的……你家同同今年也该上小学了吧” 健康与担忧: 姥姥则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家宝看着比年前结实点了,秀云你可得注意身子,别太累着……你爹(姥爷,已故)那会儿就是累的……” 债务的阴影: 不可避免地,话题还是绕到了沉重的地方。李秀云叹了口气,声音低了些:“唉,日子紧巴点倒不怕,就是……建军他娘(指吴普同奶奶)当年看病欠下的那笔债,像座山压着。年前信用社的王会计还来催利息……”她没提具体数字,但眉宇间的愁绪清晰可见。 舅舅磕了磕烟灰,眉头也皱起来:“那笔钱……确实是个大窟窿。利息滚起来吓人。你和建军……唉,难为你们了。”大姨也叹气:“有啥法子呢摊上了。慢慢还吧,总不能把人逼死。” 姥姥没说话,只是用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李秀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心疼和无奈。屋里的空气因为这沉重的话题而有些凝滞,只有炉火“噼啪”的燃烧声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闹形成鲜明对比。 这时,院子里传来自行车铃铛清脆的响声和二姨爽朗的笑声:“娘!大哥!大姐!我们来啦!” 二姨家的到来:微妙的差异 二姨李秀芬和二姨夫赵志刚推着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进了院。二姨烫着时兴的卷发,穿着崭新的呢子外套(这在农村极其少见),显得格外洋气。二姨夫赵志刚则穿着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戴着眼镜,推着锃亮的自行车,一副“公家人”的派头。车把上挂着网兜,里面装着铁盒装的饼干、玻璃瓶的水果罐头,还有一大包用红纸包着的什锦糖块。 他们的到来,让屋里更热闹了,也带来了一丝微妙的差异感。 孩子们的“福利”: 二姨一进门,就笑着招呼孩子们:“强子!壮子!大丫!石头!同同!小梅!快过来!看二姨给你们带啥好吃的了!”她打开网兜,拿出那包鲜艳的什锦糖块——里面有红绿黄各种颜色的水果硬糖,还有包裹着糯米纸的大虾酥!又拿出动物形状的小饼干!这在农村孩子眼里简直是“奢侈品”!孩子们“哇”的一声围了上去,眼睛放光。二姨夫也笑呵呵地给每个孩子分糖块和饼干,出手大方。吴普同和小梅也分到了好几块漂亮的糖和几块小动物饼干,他们小心翼翼地攥在手心,舍不得立刻吃,幸福感爆棚。 大人们的寒暄: 二姨夫赵志刚和舅舅、大姨夫(大姨夫也在后面赶到了)握手寒暄,递上“大前门”香烟,谈吐间带着镇上人的从容和一点不易察觉的优越感。他自然地坐到火炉边最暖和的位置,聊起了粮站的工作、镇上的新鲜事,以及托人弄到的“内部供应”的平价化肥票。 债务话题的回避: 当李秀云再次隐晦地提起家里的债务压力时,二姨夫赵志刚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推了推眼镜,没有接话茬,转而说起镇上信用社贷款的新政策,语气公事公办。二姨李秀芬则拉着李秀云的手,低声说:“秀云啊,别太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志刚在粮站,好歹是个正式工,我们手头……也紧巴巴的,刚添了辆自行车,花了不少……”话语里带着关切,但也明确划清了界限。李秀云理解地笑了笑,没再深说。 童趣时光:冬日暖阳下的喧闹 大人们在屋里围着火炉聊着沉重或轻松的话题,孩子们的世界则简单快乐得多。吃过二姨带来的“高级”糖果和饼干,精力过剩的孩子们在二表哥李壮的带领下,呼啸着冲出了温暖的屋子,跑到姥姥家屋后的打谷场上疯玩。 打谷场空旷,积雪被踩实了,成了天然的游乐场。 追逐打闹: 最简单的“官兵抓强盗”就能让他们跑得满头大汗,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 摔炮大战: 李壮贡献出了他珍藏的几盒“摔炮”(一种不需要明火,用力摔在地上就能炸响的小炮仗)。孩子们人手几个,兴奋地往地上、墙上、甚至别人脚边(当然是安全距离)用力摔去! “啪!”“啪!”“啪!” 清脆的炸响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孩子们夸张的尖叫和大笑。硝烟味混合着冷冽的空气,是独属于男孩子的快乐。 分享“宝藏”: 吴普同也献宝似的拿出了他初一捡到的一些“半截炮”和“瞎炮”。表哥表姐们围拢过来,熟练地用指甲剥开炮纸,倒出里面的黑火药,学着吴普同的样子,用点燃的枯草梗去点。 “嗤啦——!”金色的火花窜起,引来一片欢呼。虽然不如摔炮响亮刺激,但这种“制造”火花的乐趣同样让人着迷。 “探险”与“寻宝”: 他们还跑到场院边堆放的麦秸垛旁,试图在里面寻找有没有冬眠的刺猬(当然没找到),或者比赛谁能爬得更高。小梅和大丫则更喜欢在雪地上画画,用树枝画出歪歪扭扭的小人儿和花朵。 冬日的暖阳懒洋洋地照着,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脸冒着热气,棉袄棉裤上沾满了雪沫和草屑,但笑声纯粹而响亮,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这一刻,没有债务的忧虑,没有生活的重压,只有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间最纯粹的嬉闹和陪伴。 灶火边的温暖:姥姥的味道 傍晚时分,袅袅炊烟从姥姥家的烟囱升起。灶房里,成了女人们的战场。姥姥坐镇指挥,李秀云、大姨、二姨分工合作,准备着比年夜饭更热闹的团圆饭。 食材没有吴家年夜饭那么“硬”(指大鱼大肉),但充满了家的味道和浓浓的心意: 大铁锅里炖着喷香的小鸡炖蘑菇(用的是自家养的小公鸡和秋天采的野山蘑)。 蒸锅里热着李秀云带来的炸油条和炸年糕。 案板上放着切好的酸菜丝,准备和粉条、冻豆腐一起炒。 姥姥还特意用珍藏的白面,做了孩子们最喜欢的、点缀着红枣的花馍(造型馒头)。 二姨带来的水果罐头被打开,黄澄澄的桔子瓣泡在糖水里,是难得的甜品。 灶火熊熊,蒸汽弥漫。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女人们的说笑声,食物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暖和踏实。姥姥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一边往里添柴,一边看着忙碌的女儿们,脸上是满足而安详的笑容。偶尔,她会用烧火棍拨拉出一块烤得焦香的红薯,掰开分给在灶房门口探头探脑的孩子们。 过夜:土炕上的亲情 晚饭自然是热闹而丰盛的。两张炕桌拼在一起才勉强坐下。大盘小碗摆满了桌子,虽无山珍海味,但热气腾腾,充满了家的味道。孩子们吃得满嘴流油,大人们推杯换盏(主要是男人们喝点散装白酒),聊着家常,气氛比白天轻松了许多。债务的话题被刻意避开,仿佛被这团圆的暖意暂时融化了。 饭后,收拾停当,睡觉成了问题。姥姥家只有两铺炕。最后决定:女眷和孩子睡东屋的大炕,男人们挤在西屋的小炕。于是,东屋的炕上,上演了一出“睡通铺”的大戏。 姥姥、李秀云、大姨、二姨,加上小梅、大丫、家宝,还有吴普同(他坚持和女眷们一起睡,因为炕大暖和),七八个人挤在一铺大炕上!被褥不够厚,就两人合盖一床。孩子们被安排在炕头最暖和的位置。 虽然拥挤,却充满了别样的温馨和安全感。孩子们兴奋得睡不着,在被窝里叽叽喳喳,你捅我一下,我挠你一下。姥姥笑着呵斥:“再不睡,老猫猴子来抓人了!”这才稍稍安静下来。昏黄的煤油灯吹灭后,黑暗中,听着身边亲人们均匀的呼吸声,闻着被褥上阳光和姥姥身上特有的、混合着艾草和烟火的气息,吴普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和幸福。窗外的寒风似乎也变得遥远。 归途:甜蜜的负担 第二天上午,阳光依旧很好。吃过早饭(热了热昨晚的剩菜,又煮了锅小米粥),大人们又唠了一会儿嗑,便到了分别的时刻。大姨家离得稍近些,先带着大丫和石头告辞了。二姨和二姨夫也推上自行车准备回镇上。 姥姥拉着李秀云的手,眼圈有些发红,千叮咛万嘱咐:“回去路上慢点,看好孩子……别太累着自己,有啥难处……捎个信儿。”她悄悄把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布包塞进李秀云的口袋,里面是几张被摸得发毛的零钱——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给外孙们的压岁钱。 舅舅一直把李秀云娘几个送到村口。临别前,他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塞给李秀云:“秀云,这点钱……不多,是哥的一点心意。开春先应应急。”布袋里是卷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块钱,对于舅舅这样的庄稼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李秀云鼻子一酸,连忙推辞:“哥,不用!你留着!家里也要用钱!” 舅舅不由分说地塞到她手里:“拿着!哥家还有!建军一个人撑着不容易,别硬扛!”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带着长兄的担当。 二姨和二姨夫在一旁看着。二姨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开口。二姨夫则客气地说了句:“建军不容易,有困难说话。”便推着自行车先走了。 回程的路上,篮子轻了许多(年礼都留下了),但李秀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姥姥偷偷塞的钱,哥哥硬给的钱,像两块温暖的炭,熨帖着心口,却也沉甸甸地提醒着她肩上的担子和那个巨大的债务窟窿。孩子们则沉浸在走亲戚的兴奋和收获的喜悦里。吴普同兜里揣着姥姥、舅舅、大姨、二姨给的加起来总共几毛钱的压岁钱,还有没舍得吃完的几块什锦糖,小脸上洋溢着满足。他和小梅兴奋地交流着在姥姥家的趣事,回味着表哥表姐们的游戏和那些难得的美味。 阳光照在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反射着刺眼的光。吴普同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看母亲。母亲挎着空篮子,低着头,脚步似乎没有来时那么轻快。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回应着孩子们的叽喳,但那笑容背后,似乎藏着一种吴普同还无法完全理解的疲惫和忧虑。姥姥家的暖阳和亲情,如同冬日里短暂的篝火,温暖了身心,却终究无法融化远方那座名为“债务”的冰山。归途的脚印,在雪地上延伸,每一步,都踏在现实的冻土上。甜蜜的压岁钱在兜里叮当作响,却无法驱散母亲眉间那缕为生计和债务而生的轻愁。吴普同攥紧了兜里的糖块,那甜味似乎也带上了一丝复杂的滋味。他知道,快乐的时光结束了,回家的路,也是重新面对那座无形大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