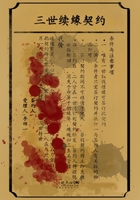第76章 有限的自由:解冻初期的校园百态
亲王府的北魏孝武皇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弦、连呼吸都仿佛要经过消毒水过滤的严格管控中,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两周后,保定农业大学的空气里,终于开始悄然注入一丝松动与缓和的气息。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同初春的冰面,在阳光持续的照射下,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纹,并逐渐扩大。 最先传来消息的是康大伟。那天下午,他像只嗅觉灵敏的猎犬,从外面打饭回来,一进宿舍门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兄弟们!重大利好!图书馆明天开始限流开放了!还有几个大教室也开了,说是给需要写论文的同学用!” 这个消息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在316宿舍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一直埋头于考研资料的李政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真的哪个教室开了有插座吗” 对于他这种需要笔记本电脑查资料的人来说,宿舍限电且没有足够插座是极大的困扰。 “具体不清楚,公告栏贴着呢,自己看去。”康大伟把饭盆往桌上一放,搓着手,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总算能换个地方透透气了,再在这宿舍待下去,我快跟李学家一样,要孵出蘑菇了。” 躺在床上面朝墙壁的李学家闻言,只是轻微地动了动,连头都没回,仿佛对外界的变化毫无兴趣。 紧接着,学校机房有限开放的通知也下来了。虽然需要预约,上网时间严格限制,且电脑数量有限,但这对于几乎与网络世界隔绝了半个多月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吴普同感到一种久违的、名为“希望”的东西,正随着这些逐步放宽的措施,一点点重新回到身体里。他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和机房的电脑。他的两篇毕业论文——《关于集约化养猪场饲料效率提升的探讨》和《县域农产品流通体系优化研究——基于经济管理视角》——都只完成了开题和初步框架,大量的文献查阅、数据整理和文字撰写工作还堆积在那里。前两周的完全禁足,几乎让论文工作陷入停滞,这让他内心焦灼不已。 活动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选择权的回归。宿舍不再是唯一的天地,校园里那些熟悉的场所,重新向他们敞开了怀抱,尽管这怀抱还带着诸多限制——图书馆需要登记、测温,并限制在馆人数;教室需要保持间隔就坐;机房需要提前预约,每人每天限时两小时。而且,那道象征着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学校大门,依然紧闭,持枪(体温枪)的门卫依旧表情严肃,严禁任何人无故出入。这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是在划定圈子内的放风,但比起之前纯粹的“禁闭”,已然是天壤之别。 在新的政策下,316宿舍的六个人,仿佛六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凭借着各自不同的质量和形状,迅速沉向了不同的水域,呈现出迥异的生存状态。 吴普同无疑是其中最忙碌、也最目标明确的一个。他像一只重新储备过冬粮食的松鼠,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上午,图书馆刚开门,他就带着笔记本和水杯,成为第一批入馆者。熟悉的书香和旧纸张的味道,暂时驱散了消毒水的气味,让他感到一种心神上的安宁。他在畜牧兽医和经济管理类的书架间穿梭,按照之前列好的书单,寻找着那些关乎他论文命运的参考书籍。有时为了找到一本关键的文献,他需要在密集的书架间徘徊许久,找到时那种喜悦,不亚于发现宝藏。下午,他会转战到开放的自习教室,摊开资料和稿纸,开始梳理思路,进行艰难的撰写工作。偶尔,他也会成功预约到机房的时段,利用那宝贵的两小时,在网上搜索最新的行业数据,或者将手写的文稿一点点录入电脑。键盘敲击的声音,在他听来,比任何音乐都更令人安心。这种充实而有序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马雪艳的思念和对疫情的焦虑。 与吴普同的勤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学家的“以不变应万变”。即便图书馆、教室重新开放,他依旧雷打不动地宅在宿舍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的床铺和到门口取饭的那几步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面朝里侧躺着,不知道是醒是睡。有时他会坐起来,拿着一本不知道什么书,半天也不翻一页,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康大伟几次叫他一起出去“放放风”,他都只是懒洋洋地摇摇头,嘟囔一句“没劲”或者“外面不安全”,便再无下文。他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或者说屈服于这种极度收缩的生活状态,并将它内化为了自己的舒适区。 康大伟则像是被骤然松开了链子的哈士奇,迫不及待地要将之前憋闷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他迅速和班上其他几个同样“耐不住寂寞”的男生搅和在一起,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玩扑克。他们通常聚集在某个宿舍(只要不被值班老师抓到严格意义上的“串门”),把桌子拼起来,就能鏖战整个下午,吆喝声、拍桌声、赢牌的欢呼和输牌的哀叹,能穿透门板传到走廊。除了扑克,学校里那个规模很小、电脑配置老旧、但在当前环境下却显得无比珍贵的小网吧,也成了康大伟和他的“战友们”时常光顾的据点。虽然上网限时,网速慢得像蜗牛,而且空气污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沉浸在cs或者《传奇》的世界里,通过虚拟的厮杀来宣泄现实中无处安放的精力。偶尔,他们甚至会铤而走险,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搞到通宵的资格,在屏幕的微光下度过一个个黑白颠倒的夜晚。 “老吴,别整天对着那些破书了,走,跟我们打牌去!三缺一!”康大伟有时会试图拉拢吴普同。 吴普同总是头也不抬地摆摆手:“不了,论文deadline要命呢。你们玩吧。” “没劲!”康大伟撇撇嘴,转而看向张卫平的空铺位,“卫平这小子,又跑没影了,神出鬼没的。” 张卫平的确是个特殊的存在。即使在管控放松后,他依然保持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格。没人清楚他具体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有时会在宿舍突然出现,默默地收拾点东西,或者吃个饭,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问他,他也只是含糊地说“出去转转”或者“有点事”。他的床铺总是整整齐齐,个人物品极少,仿佛随时准备离开。这种神秘感,在如今相对透明的环境下,显得格外突兀。 而杨维嘉和李政,则成为了开放自习教室的忠实拥趸。对他们这两个考研党来说,宿舍环境过于散漫,缺乏学习氛围。如今教室开放,简直是久旱逢甘霖。他们每天早早便背着塞满复习资料的双肩包,提着暖水瓶,如同上班打卡一样,准时出现在固定的自习教室,一坐就是一天。那里聚集了许多和他们一样目标明确的同学,虽然彼此不说话,但那种集体埋头苦读的氛围,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鞭策和压力。只有在吃饭和晚上熄灯前,他们才会返回宿舍,脸上带着高强度用脑后的疲惫,以及一种时间紧迫的焦虑感。 “李政,你数学复习到哪儿了”晚上,杨维嘉可能会一边泡着脚,一边问。 “概率论第二轮。感觉时间不够用了。”李政揉着发胀的太阳穴。 简单的交流后,往往是一阵沉默,各自消化着压力。 吴普同在这种新的节奏下,虽然忙碌,内心却比之前充实了许多。论文工作的推进,给了他一种掌控感和成就感,仿佛在混乱的外部世界中,他依然能把握住自己前进的方向。当然,他并没有忘记马雪艳。在机房预约成功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给她宿舍打电话,虽然接通率依然不高,但比起之前完全失联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偶尔能通上话,他会分享自己论文的进展,听她抱怨乳品厂依旧严格的封闭管理,彼此加油打气。他知道,她那边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让他心疼,也让他更加珍惜自己这来之不易的、有限的自由和能够推进学业的机会。 校园,就这样在一种“有限解冻”的状态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分层的生机。有人在书山学海中奋力跋涉,有人在虚拟世界里寻求慰藉,有人选择继续龟缩,有人则行踪成谜。共同的困境似乎过去了,个体的选择和轨迹再次分叉。那道紧闭的校门依然提醒着他们,真正的自由尚未到来,但至少,在这有限的围墙之内,他们重新获得了一点选择如何度过时间的权利,一点让生活回归“正常”轨道的微弱希望。而吴普同,正牢牢抓住这希望,在弥漫的消毒水气味尚未完全散去的图书馆和教室里,为他即将到来的毕业,也是为他和马雪艳的未来,默默地积蓄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