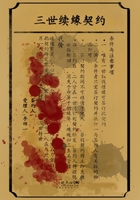第77章 尘埃里的日常:麻木、习惯与遥远的思念
亲王府的北魏孝武皇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时间,在这座被按下慢放键的校园里,仿佛变成了某种粘稠的、近乎凝固的液体。它依旧向前流淌,却失去了往日的轻快与节奏,只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缓慢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推进着。曾经尖锐的恐慌、最初的焦虑、以及对解封的急切期盼,都在这漫长而单调的重复中,被一点点磨平了棱角,沉淀为一种更深沉、也更无奈的底色——麻木,以及随之而来的习惯。 人们,包括吴普同和他的室友们,似乎都逐渐“习惯”了。 习惯,成了这段特殊时期最强大的生存法则。 他们习惯了每天清晨或傍晚,那准时响起的敲门声和“测体温了”的例行公事。不再需要催促,大家会自觉地排好队,如同条件反射般伸出额头,等待那一声决定今日心绪的“嘀”响。数字正常,心中一块小石落地;数字稍有波动,即使最终无恙,也会带来一阵短暂的心悸,随即又迅速被“习惯了”的麻木所覆盖。 他们习惯了不扎堆、不聚集。图书馆里,即使开放了更多的座位,学生们也会下意识地选择相隔最远的位置,仿佛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半径一米的排斥场。教室里,稀疏的人影分散在偌大的空间里,各自守着一方书桌,像是星空中彼此遥远的孤星。就连在食堂打饭排队,那地上的一道道黄线,也早已内化为行为准则,无人逾越。 他们习惯了一米线和口罩。那白色的、蓝色的、或厚或薄的布料,成了脸上第二层皮肤,遮住了表情,也仿佛隔断了部分情绪的流通。呼吸变得沉闷,眼镜容易起雾,但这些不便,也早已被纳入“正常”生活的范畴。取下口罩,反而会感到一丝不习惯,仿佛暴露在空气中是不安全的。 他们习惯了通过那根细细的电话线与外界保持脆弱的联结。316宿舍的电话,依旧是最繁忙的“战略资源”。吴普同习惯了在特定时段,抱着微弱的希望反复重拨马雪艳宿舍的号码,习惯了通话时信号可能的突然中断,习惯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捕捉她那熟悉又仿佛遥远的声音。他也习惯了每周固定给家里打电话,听父亲用那不变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讲述着西里村平静而封闭的日常,那是一种与校园截然不同的、近乎停滞的安稳。 然而,习惯,并不意味着舒适,更不意味着忘却。 学校那道紧闭的、由铁栏杆和严肃门卫把守的大门,像一个永恒的提醒,矗立在视野可及的远方。它象征着真正的自由,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世界。吴普同有时去离校门较近的开放教室自习,会不自觉地望向那边。他看到门外偶尔驶过的汽车,看到远处街道上稀疏的行人(虽然也都戴着口罩),看到更远处天空下模糊的城市轮廓。那些曾经寻常的景象,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而遥远。围墙与栏杆之内,是他们被划定的、安全的“孤岛”;之外,是那个他们曾经属于、如今却感觉隔了一层毛玻璃的、充满未知的世界。这种物理上的隔绝,带来的是心理上深刻的疏离感与囚禁感。 对恋人的思念,对家人的想念,并未因习惯而淡化,反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和不确定的等待中,发酵得更加浓烈,如同陈年的酒,带着苦涩的醇厚。 吴普同对马雪艳的牵挂,已经细密地织入了他每一天的纹理。他会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某个可能与乳品行业相关的数据时,下意识地想:“这个或许对雪艳有用。”会在吃饭时,想象着她此刻在厂区食堂吃着什么,是否安好。会在深夜放下笔,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计算着高阳的方向,想象着她是否也正望着同一片天空,被同样的思念缠绕。每一次短暂的通话,都像是给即将耗尽电量的电池进行的一次微弱充电,支撑着他继续在这麻木的日常中坚持下去。 “我们厂里最近在搞什么‘安全生产月’活动,还要写心得,烦死了。”马雪艳在电话里抱怨,声音里带着疲惫。 “总比闲着好。”吴普同安慰道,同时分享着自己的进展,“我论文的数据分析部分快弄完了,就是参考文献还差几篇,图书馆找不到,机房又限时……” “那你慢慢来,别着急。我们这边……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会过去的,再坚持一下。”他重复着这苍白却唯一的安慰,话语出口,自己都觉得无力。 每天,校园广播和宿舍那台旧电视里的新闻播报,依旧准时响起。那些关于新增病例、防控措施、专家解读的熟悉声音和画面,构成了他们了解外部疫情的唯一官方窗口。这些消息,感觉离自己很近,因为它切实地影响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又感觉很遥远,因为那些数字和地名,被局限在小小的屏幕和喇叭里,与围墙内相对平稳(尽管压抑)的日常形成了某种割裂。然而,偶尔播报的某个死亡病例数字,或者某个熟悉城市名称的出现,还是会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破麻木的表层,让吴普同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一天,他在新闻里看到一个模糊的、关于一线医护人员因公殉职的简短报道,画面一闪而过,没有细节,只有沉重的音乐和肃穆的语调。那个傍晚,他独自在开放教室待到很晚,没有开灯,只是坐在逐渐昏暗下来的光线里,望着窗外空无一人的操场。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虚无感和悲伤攫住了他。个体的挣扎、思念、乃至生命,在这席卷全球的疫情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他想起不知在哪里看到过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承受着这“尘埃”的重量。这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瞬间,是未来史书上可能寥寥数笔带过的“某某年疫情”,但对他们这一代人,对于被困在校园、工厂、村庄里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是青春中无法磨灭的、灰暗的一笔。将来的历史,是否会真正记住这一刻的惶恐、压抑、坚韧与卑微的期盼 回到316宿舍,气氛依旧是分层的。康大伟和几个牌友刚结束一场“战斗”,宿舍里还残留着烟草和泡面混合的味道,他正眉飞色舞地计算着今晚的“战利品”——几包零食。李政和杨维嘉刚从自习室回来,脸上带着倦容,低声交流着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李学家依旧面朝墙壁,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张卫平的床铺依旧是空的。 吴普同默默地洗漱,爬上床铺。宿舍的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熟悉又令人窒息的混合气味。他听着室友们或兴奋或疲惫的呼吸声,想着远方的恋人和家人,想着那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自由呼吸的将来。麻木之下,是暗流涌动的思绪;习惯背后,是未被磨灭的渴望。这尘埃里的日常,还在继续,缓慢地,沉重地,指向一个未知的终点。而他们,只能在这巨大的时代涡流中,努力保持着内心的方寸之地,等待着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哪怕那一天,在重复的日出日落中,显得那么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