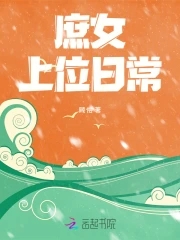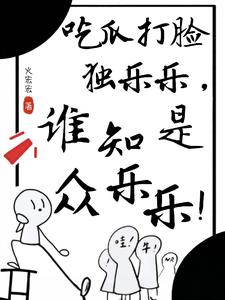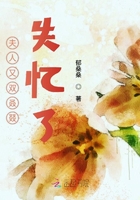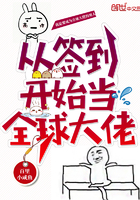典苍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嫩江县郊外,一片废弃的校舍被紧急征用,成为了临时的师部前进基地兼新兵整编点。尚未完全消散的晨雾中,断壁残垣上覆盖着大量的伪装网,与周围新挖掘的、纵横交错的防空壕共同构成了一幅紧张的临战图景。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味、消毒水的气味,以及一种无声的压抑。 廖奎跟随着人流,沉默地排队等待登记核查。他的目光扫过周围,那些指向天空的、简陋的高射机枪阵地,无声地诉说着对江北那头钢铁巨兽空中优势的深深忌惮。登记处设在一个残破的教室里,负责的军官表情严肃,眼神锐利如鹰,反复核对着每个人的档案,尤其是“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两栏。 “廖奎,原第七农场职工,兽医…家庭成分,富农。”军官念到这里,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抬眼审视着廖奎。 廖奎心头一紧,面上却维持着平静。他知道这个成分在此刻意味着什么。 “师部培训,综合评定,第一。”军官继续念道,语气略微缓和,又看了看廖奎那远超普通新兵的沉稳气质和强健体魄,“嗯…去那边领装备,编入机动医疗队。” “是。”廖奎应声,暗暗松了口气。他注意到,排在他后面一个同样成分不好、但无技术特长的中年人,就被反复盘问,最终被调整去了需要更严格监督的工兵连。时代的烙印,在战时的整编中,依旧清晰而残酷。 领取装备的地方更像一个混乱的物资分发点。到手的军装是混纺的,颜色深浅不一,袖口甚至有些磨损。配发的急救包瘪瘪的,里面只有寥寥几卷绷带、一小瓶磺胺粉和几片止痛药,显得捉襟见肘。最让廖奎注意的是那套医疗器具——止血钳、手术剪等,虽然经过消毒,但细看之下,上面有着细微的划痕和使用过的痕迹,显然是经过回收再利用的。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现了此时此地物资的极端匮乏与战时的将就。 整编后的简短集会上,一位师部参谋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进行动员,除了强调战场纪律外,更反复提及了来自最高层的指示: “…同志们!要深刻领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在失去后方支援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独立生存的准备!要依靠群众,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坚持到底!” 这话语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被孤立,可能面临极端的补给困难,生存的压力不仅仅来自敌人的枪炮。 或许是因为他在师部培训时展现出的惊人冷静、精准的操作(源于系统技能的底子)以及那份远超同龄人的沉稳,廖奎被破格任命为新组建的机动医疗小队的小组长。他手下有另外两名卫生员,一个是从公社赤脚医生抽调来的年轻人,眼神里还带着些紧张和好奇;另一个是年纪稍长、有些经验但理论基础薄弱的老兵。 “廖组长,我们…都听你的。”年轻的卫生员看着廖奎,语气带着依赖。 廖奎点了点头,没有多言。这份任命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这两个战友的生命负责。 等待分配的间隙,他听到旁边几个蹲在一起抽烟的老兵在低声交谈,话语顺着风隐约飘来: “…妈的,听说北边那帮家伙,坦克跟铁王八似的,炮管子粗得能钻进去人…” “都得机灵点,看见信号就得往反坦克壕里跳…” 这些零碎的议论,比任何战前动员都更具体,更血腥。廖奎默默地听着,对即将踏上的战场有了更清醒、也更残酷的认知。那不再是训练场上的模拟,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钢铁与血肉的碰撞。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分发到的那套带有使用痕迹的医疗器具,又感受了一下意识中那两个新生的技能——【明镜止水】与【战场生存本能】。前路艰险,但他必须活下去,也必须尽可能地,让身边更多的人活下去。他抬起头,望向北方阴沉的天际,目光沉静,如同冰封的湖面,下面却涌动着决绝的暗流。 香港半山区,梅道一号的顶层公寓内,夜色被隔绝在厚重的丝绒窗帘之外。萧雅姿——此刻已是完全体的“萧亚轩”——独自坐在客厅昂贵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身旁那台造型典雅的根德牌收音机正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她纤细的手指缓缓调节着旋钮,bbc世界新闻的播报员用冷静的英式口音叙述着东南亚某地的游击战,随后切换到radio moscow,则是充满火药味的、对“全球解放运动”的声援。她试图从这些碎片化的国际讯息中,捕捉到一丝关于北方那片黑土地上冲突的蛛丝马迹,哪怕只是一个侧影。手边摊开的几份香港英文报纸,对中苏边境的报道大多语焉不详,谨慎地引用着路透社或美联社的消息,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微妙的中立与观望。香港,这座浮华与动荡并存的孤岛,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扮演着独特而暧昧的信息中转角色。 萧亚轩关掉收音机,室内陷入一片沉寂。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俯瞰着维多利亚港依旧璀璨,却无法照亮她心底忧虑的灯火。是时候了。 她集中精神,意识沉入系统空间。 空间里,谢薇——或许从她决定离开北大荒的那一刻起,心理上已开始向“谢亦菲”过渡——正安静地坐在主屋的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枚父亲的军功章。她的行囊已经收拾好,不多,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绝对私人的小物件,包括那本几乎被翻烂的英语笔记。 “薇薇,准备好了吗”萧亚轩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声音放得很轻。 谢亦菲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崩溃,只剩下一种认命般的平静,和深藏其下的离殇。“嗯。”她轻轻点头。 “我们最后确认一次。”萧亚轩语气严肃,心念一动,空间的影像切换,投射出外界土坯房周边的实时景象。透过那扇破旧窗户的缝隙,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场保卫科的人员,在王司冲的带领下,正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地进行新一轮的、更为严格的户籍与人员核查。他们的表情冷硬,盘问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肃杀的气氛,即使隔着空间屏障,也能感受到。 “看到了吗我们必须走,立刻。”萧亚轩斩钉截铁地说。眼前的景象,彻底打消了任何一丝侥幸的念头。 谢亦菲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象变得陌生而危险,用力抿了抿嘴唇,再次点头。 没有过多的告别仪式,对这片土地,对那间承载了短暂温暖与巨大悲痛的土坯房。萧亚轩握住谢亦菲的手,另一只手提着那个轻便的行囊,心念锁定已记录的空间坐标——香港半山区公寓,主卧室。 轻微的晕眩感传来,是空间转换时熟悉的失重。下一秒,脚踏实地的感觉回归,周遭的景象已彻底改变。 低矮、冰冷、弥漫着土腥味的土坯房,变成了铺着柔软羊毛地毯、弥漫着淡淡香氛、灯火通明的奢华卧室。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香江璀璨的夜景。 谢亦菲怔怔地站在原地,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她的目光扫过房间里那些在她看来不可思议的物件:洁白如玉的抽水马桶(萧亚轩之前简单提过)、发出轻微嗡鸣的冰箱、那个能放出人影和声音的“电视机”……这一切,与北大荒需要凿冰取水、烧炕取暖、夜里只有一盏如豆油灯的生活,形成了天壤之别。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她在系统“投影仪”里见过,却从未亲身感受过的世界。 萧亚轩理解她的茫然,轻声解释道:“这是抽水马桶,用完后按这个冲水…冰箱是保持食物新鲜的,但不能放太久…电视机…暂时先不看。”她耐心地指引着,同时提醒,“在这里,水电都是要钱的,用多了账单会很高,和咱们在农场时不一样。” 这简单的提醒,像一根针,刺破了谢亦菲恍惚的状态。她意识到,这里的一切都标着看不见的价格,这是从计划经济的集体供给,向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个体承担的初步过渡,她必须开始学习适应。 传送过程顺利得近乎平淡,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当卧室的门轻轻关上,将香港的夜光与北大荒的回忆暂时隔绝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才如同潮水般漫上心头。 她们安全了,暂时远离了北方的枪炮与肃杀。 但她们也真正离开了那片浸透着父亲鲜血、埋葬着青春记忆的黑土地。 谢亦菲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蜿蜒的车河与远处霓虹闪烁的港岛,手指在玻璃上无意识地划着。她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被这陌生的繁华填满,却又更加空洞。 萧亚轩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她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深知离乡背井的滋味。此刻,任何安慰都是苍白的。她们能做的,就是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带着过往的伤痕与未来的希望,挣扎着,活下去。 远行已然开始,归期,渺茫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