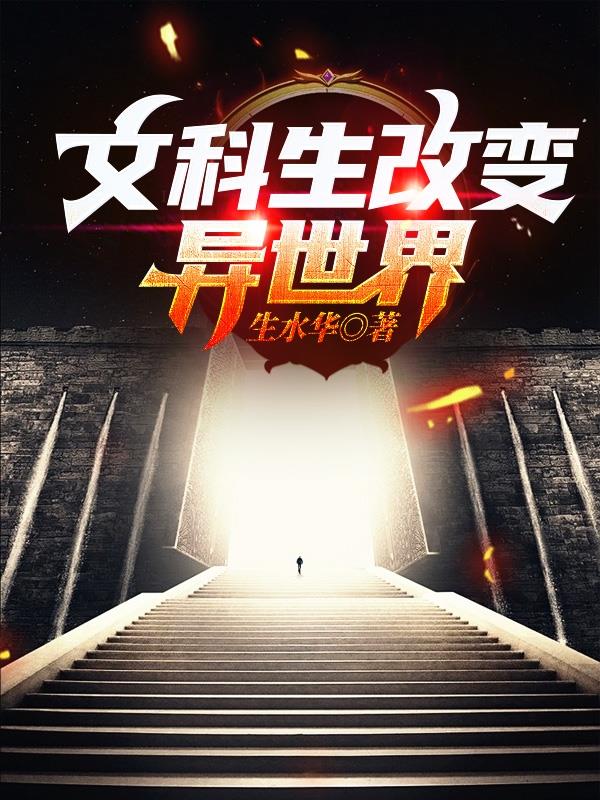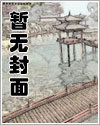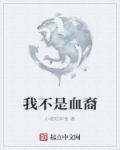我困了我要睡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 拉萨的日光,一如既往的炽烈与纯净,照耀着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也照耀着山下那座日益繁忙的宣慰使司衙门。帝国的统治,如同这高原的溪流,看似平静,却在持续不断地冲刷、浸润着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陆弘毅坐镇于此,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医者,对西藏这具庞大而独特的“躯体”,进行着精细而耐心的“调理”。 权柄的细化:从宣慰使司到宗溪 帝国的统治机器开始向基层延伸。陆弘毅并未急于全面推行内地的行省州县制度,而是采取了更为务实的过渡策略。他大致沿用了西藏原有的“宗”(相当于县)和“溪”(相当于庄园或更小的行政区划)的行政框架,但注入了帝国的灵魂。 流官知宗的派遣: 首批经过紧急培训、略通藏语或配有通译的流官,被任命为拉萨周边几个关键“宗”的 “理事同知” 或 “协理通判” 。他们的首要任务并非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 “摸清家底”——详细登记所辖宗溪的人口、户籍、田亩、牲畜、物产。这个过程充满了博弈与试探,本地头人、管家们或明或暗的抵触时有发生。流官们依靠驻军在侧的战略威慑,以及公平处理几起典型纠纷(如草场争端、债务诉讼)所建立的初步威信,艰难地打开着局面。 《赋役折色暂行条例》的推行: 在初步清查的基础上,陆弘毅颁布了赋税新政。没有直接照搬内地的银两或实物税,而是创造性地规定了 “赋役折色”——允许百姓根据自身情况,以青稞、酥油、牛羊、药材、皮张等本地产物,折价抵充赋税和劳役。同时,明确废除了旧政权时代许多名目繁杂、随意性极大的摊派和“乌拉”差役。此举虽减少了帝国初期的直接税收,却极大地减轻了底层农奴和牧民的负担,赢得了广泛的民心,从根本上动摇了旧贵族的经济特权根基。 驿传体系的帝国化: 以拉萨为中心,通往昌都、林芝、墨脱乃至后藏日喀则、藏北那曲的主要驿道被纳入帝国管辖。设立了标准的驿站,配备了固定的驿卒和马匹,传递公文军报,也方便商旅往来。这条信息与物资的动脉,成为了帝国控制西藏的有形纽带。 军事的深耕:从镇守到屯垦 格桑的镇守总兵官府,同样忙碌不息。单纯的军事威慑已不足够,军队开始更深地融入这片土地。 战略要地的堡垒化: 在巩固拉萨周边大营的同时,格桑派出工兵部队,在藏北通往青海的咽喉要地(如那曲)、后藏与前藏的交界处(如江孜)等地,选择险要位置,开始修筑小型的、永久性的军事堡垒和烽火台。这些据点如同帝国的神经末梢,延伸向西藏的各个方向,既预警外患,也监视内忧。 “以屯养兵”的尝试: 借鉴金川和昌都的经验,格桑开始在拉萨河谷、年楚河谷等水土相对丰美之处,划出部分土地,建立军屯点。留守的士兵在操练之余,化身农夫,开垦种植,饲养猪羊。这不仅是为了补充军粮,更是一种长期驻守的姿态,意味着帝国军队准备在这里世代扎根。这些军屯点也成为了向周边牧民、农民示范先进农耕技术的窗口。 “蕃勇营”的扩编与整训: 在格桑的“金川忠威营”成功范例基础上,陆弘毅批准从归顺的藏兵中,择优招募健儿,组建更大规模的 “西藏忠勇营” 。由帝国军官负责指挥和纪律训练,装备帝国制式武器,但允许其在非正式场合保留部分本民族习惯。这支本土化辅助部队的形成,不仅增强了帝国在藏的军事力量,更给予本地勇士一条晋升通道,有效分化了潜在的抵抗力量。 文化的涓滴:潜移默化的渗透 文化的融合,在无声处悄然进行。 官学的困境与突破: “拉萨官学”的运营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只有少数底层平民和与帝国合作密切的贵族子弟入学。为了打破僵局,陆弘毅采取了变通措施:他请求朝廷,特设 “西藏恩科” ,承诺官学中成绩优异者,可不经内地重重科举,直接授予在藏流官职位或推荐入国子监。同时,官学不仅教汉文,也聘请喇嘛教授藏文和佛学基础知识,展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平等与尊重。利益的驱动与态度的转变,使得入学人数逐渐增多。 医疗的仁心: 随军医官在拉萨开设了第一家面向公众的“惠民药局”。他们带来的内地医术,尤其擅长治疗伤寒、外伤和一些儿科疾病,效果显着,且收费极低甚至免费。一剂汤药治愈一个孩童,一次针灸缓解一位老人的痛苦,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举,比千言万语的政治宣传更能打动人心,无形中消解着隔阂。 历法与节气的引入: 宣慰使司开始每年颁布帝国《时宪历》,虽然藏历依旧并行,但官方文书、赋税征收、大型工程动工日渐采用农历纪元。这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是在统一着这片土地的时间刻度,象征着与帝国中枢的节奏同步。 暗流的应对与未来的隐忧 治理并非一片坦途。旧贵族们虽然表面顺从,但对其特权的丧失心怀不满,暗中串联、消极对抗的情况时有发生。青海的蒙古王公对帝国直接控制西藏感到不安,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摩擦试探开始出现。遥远阿里地区的土王,态度依然暧昧不明。 陆弘毅对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面通过韩震的情报网络严密监控,对任何试图挑动叛乱的苗头予以坚决、快速的打击;另一方面,则继续加大政治分化与拉拢的力度,对合作者给予实利,对观望者耐心争取。 他站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看着磕长头的信徒,看着穿梭的商旅,也看着巡逻的帝国士兵。他知道,帝国的统治才刚刚开始,根基尚浅。他将一份新的奏疏交给信使,内容是关于请求朝廷派遣更多精通藏语、熟悉边情的官员,以及拨款兴修拉萨水利,根治河谷水患的建议。 帝国的阳光,已经普照雪域,但要融化千年冻土,培育出忠于帝国的禾苗,仍需更多的耐心、智慧与投入。拉萨,这座圣城,正站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它的未来,将在这日复一日的精细治理与艰难融合中,被慢慢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