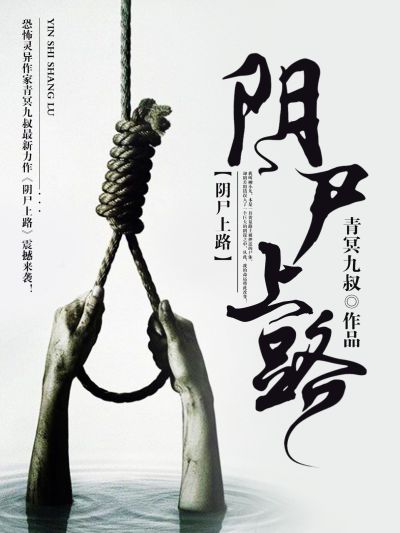峰上生枫蜂作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金属灼烧后的刺鼻气味。那两架被暴力摧毁的自动化机枪残骸兀自冒着缕缕青烟,扭曲的枪管和碎裂的支架无声诉说着方才电光火石间的致命袭击。 昂热站在废墟之间,西装依旧笔挺,与周围的狼藉格格不入。但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灰蓝色的眼眸里不再是平日的绅士从容,而是沉淀着冰冷的风暴。他的视线从机枪残骸上移开,落在几步之外那个穿着黑色牧师袍的身影上——艾伦威尔逊,此刻正微微垂首,双手交叠放在身前,一副悲天悯人的虔诚姿态。 “你早就知道”昂热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有人用这种下作手段伏击他,他并不十分意外,漫长的人生中他经历过太多。真正让他动怒的,是这东西差点害死他的学生。犬山贺那孩子,刚才竟想用身体替他挡子弹……一想到这个,他胸腔里的怒火就几乎要冲破理智。 艾伦威尔逊抬起头,脸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受感召般的肃穆。“是主的指引,让我今日途经此地,昂热校长。”他的声音温和而充满确信,仿佛在陈述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 主的指引昂热在心底发出一声冰冷的嗤笑。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前这个英国深层官僚的本性,那些藏在十字架和圣经背后的,是精密的算计、冷酷的利益和浸透在血脉里的权谋。他锐利的目光如同手术刀,试图剥开那层虚伪的牧师长袍。 但他还是压着性子,带着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嘲讽问道:“那么,你那位‘主’的下一步指引是什么能不能找到那个想害死我学生的混蛋”他特意加重了“我学生”三个字,如同龙在宣示逆鳞。 艾伦的脸上浮现出更深的悲悯,他轻轻划了个十字,动作优雅标准。“当然,尊敬的昂热校长,”他的语气笃定,“请您相信,那位混蛋会遭报应的。” “哼,”昂热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嘴角勾起一个毫无笑意的弧度,紧紧盯着艾伦,“报应”他重复着这个词,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诮,“这种充满……宿命论和天道循环色彩的词,很难想象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威尔逊。” 他微微前倾身体,虽已是老人,但那瞬间散发出的压迫感却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他一字一顿,声音低沉而危险:“我认识的你,只相信文件和档案,相信‘必要之恶’,相信藏在阴影里的交易。什么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于……‘报应’了” 艾伦威尔逊面对昂热那毫不掩饰的讥讽,脸上的悲悯神色丝毫未变,仿佛早已料到会遭遇这样的质疑。他甚至还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声温和而包容,却更显其深不可测。 “校长阁下,您误解了。”他缓声道,指尖摩挲着胸前冰冷的十字架吊坠,“我从来都是信奉上帝的,从未改变。只是我比许多人都更明白一个道理:主的恩赐如同阳光雨露,普照大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躺在原地,指望杂草会自动枯萎,良种会自动丰收。” 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迎上昂热锐利的审视:“有时,园丁也需要亲手拔除莠草,为主想要的花园扫清障碍。这并非背离信仰,而是践行信仰的一种方式。”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奇异的、自我合理化的坚定,仿佛他口中那带着血腥气的“拔除”是某种神圣的仪式。 看着他这副样子,昂热仿佛看到了中世纪那些一手持剑、一手举着十字架的骑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发动“圣战”的十字军——以神之名,行杀戮之事。但剥开这层宗教的外衣,内核依旧是那该死的、精于算计的深层官僚。他对艾伦这套说辞不置可否,也懒得再与他进行神学或哲学上的辩论。 他的注意力早已转移。目光越过艾伦,落在了不远处正被几位义女小心翼翼清理手臂上擦伤的犬山贺身上。只是皮外伤,但看到年轻人因自己而涉险,昂热心头那股无名火依旧在灼烧。 犬山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边凝滞的气氛,尤其是那个牧师打扮的艾伦威尔逊似乎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眉头紧蹙,忍着疼痛,强行支撑着站了起来,不顾义女们担忧的低呼,步履有些蹒跚却坚定地走到了昂热身边。 “老师。”犬山贺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伤后的虚弱和一种不容置疑的郑重。他微微侧身,用身体挡住了艾伦可能投来的视线,凑到昂热耳边。 昂热配合地微微俯身。 犬山贺的气息喷在他的耳廓,用几乎只有气流才能传达的声音,快速而清晰地说道:“在日本没有人值得你信任,去找……那个男人,他还活着,他知道一切。” 昂热没有追问细节,也没有表现出过度的震惊。只是微微点头,轻轻拍了拍犬山贺未受伤的肩膀,是一个无声的安抚和“我知道了”的示意。他看着依旧杵在原地,丝毫没有离开意思的艾伦威尔逊,眉宇间的不耐烦几乎要凝成实质。他冷冷开口,驱赶的意味毫不掩饰:“威尔逊,你的‘主’的指引既然已经传达完毕,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艾伦闻言,脸上那副悲天悯人的神情如同潮水般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好奇与慵懒的微笑。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双手抓住牧师袍的领口,向两边一分,利落地将这件黑色的外袍脱了下来,随手搭在臂弯。 袍子之下,赫然是一身剪裁得体、面料考究的经典英国公务员装扮——灰色的三件套西装,熨帖的白衬衫,一丝不苟的领带,与他刚才的宗教使者形象判若两人。他仿佛卸下了一个角色的戏服,瞬间变回了那个在唐宁街和白厅走廊里游刃有余的深层官僚。 “昂热校长,关于这一点,”他微微颔首,用那种惯常的、带着点迂回腔调的官方式语气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先前关于‘指引’的部分,可以视为一个……呃,独立的议程项。而现在这项议程已经圆满结束。” 他转而面向犬山贺,笑容不变,话语却开始绕起圈子:“至于我本人为何仍在现场,这涉及到一些后续的、非官方的考量。犬山先生,在不影响您处理当前……嗯,‘突发状况’的前提下,我是否可以冒昧地咨询一下,贵俱乐部,‘玉藻前’,预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营我个人对此类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场所抱有相当的兴趣,原则上很希望能有机会亲身体验。” 他稍稍停顿,似乎在斟酌词句,继续用那种令人昏昏欲绕的腔调说道:“此外,如果流程上允许,并且不涉及任何……呃,商业机密或不适当的范畴,我对于犬山家旗下相关联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那些动态影像记录的工作室,它们的运作模式也颇有了解的兴趣。不知是否有合适的渠道,可以安排一次初步的、非正式的观摩学习这纯粹是基于个人对文化产业多样性的欣赏……” “艾伦!”昂热低沉的声音打断了他。只看艾伦眼神的变化和提起的话题,昂热就知道这家伙那深入骨髓的享乐主义本性又发作了,转头就开始惦记着风月场所。 昂热本不想再搭理他,但眼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家伙开始骚扰自己那刚经历惊魂、身上还带着伤的学生(尽管犬山贺也已不再年轻,但在昂热眼中,他依然是需要庇护的后辈) “你的‘咨询’和‘观摩’请求,原则上被驳回了。”昂热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艾伦的官腔扔了回去,语气却冰冷如铁,“现在是非讨论时间。你,跟我离开。这里需要空间进行善后工作,而伤员,”他看了一眼犬山贺,“需要休息,而不是应付无休止的‘流程咨询’。” 说罢,他拽着艾伦,无视对方脸上那略显错愕但迅速恢复成公式化微笑的表情,,强行将他拖离了这片是非之地。 昂热几乎是半押送地将艾伦威尔逊带离了玉藻前俱乐部那片弥漫着硝烟与紧张气息的区域,来到了外面相对清静些的街巷。夜色已然降临,街灯在潮湿的空气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 “你的专车呢”昂热松开手,语气不容置疑地问道,仿佛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应该有随叫随到的交通工具。 艾伦整理了一下被昂热拽得有些歪斜的领带,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公务员式微笑:“尊敬的校长,这个时间点,官方配属的交通工具早已下班,回归车队统一管理了。这是流程,您明白的。”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里优雅地掏出一把车钥匙,在指尖轻轻一晃,“不过,我个人的代步工具倒是恰好在这里。” 他话音刚落,昂热已经毫不客气地伸手,几乎是抢一般将钥匙从他指尖取走。动作之快,让艾伦脸上的微笑都僵硬了零点几秒。 昂热顺着钥匙遥控灯闪烁的方向望去,看到了一辆静静停靠在路边的银色宾利欧陆gt(2008年款),流畅的线条在夜色中散发着低调而奢华的光芒。他挑了挑眉,径直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室,同时丢下一句:“征用了。” 艾伦这时才像是回过神来,快步走到驾驶座窗边,微微俯身,脸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介于为难与礼貌之间的表情:“昂热校长,这……恐怕不太符合规定吧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我会把钱打到你账户上。”昂热一边熟悉着车内豪华的配置,一边头也不抬地打断他,“三倍。” 艾伦张了张嘴,似乎准备开始他那套关于“资产评估”、“折旧率”以及“潜在使用价值损失”的冗长计算和官僚话术。 昂热没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加码,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十倍。” 瞬间,艾伦脸上所有程式化的为难和准备展开辩论的表情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心实意的、几乎是焕发容光的微笑,干脆利落地应道:“成交。祝您用车愉快,校长。”那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就在这时,一阵低沉而富有力量的摩托车引擎声由远及近,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一辆造型夸张的杜卡迪怪兽摩托车以一个略显狂野的姿态停在了宾利旁边。车上挤着三个高大的年轻男孩——驾驶位上金发张扬的恺撒加图索,中间是面无表情但坐得笔直的楚子航,最后面则是紧紧抱着楚子航腰、一脸惊魂未定又带着点兴奋的芬格尔。三个大男人挤在一辆摩托上,场面看起来有些滑稽和拥挤。 恺撒摘下头盔,甩了甩金色的头发,看向宾利驾驶座里的昂热,又瞥了一眼旁边笑容可掬的艾伦威尔逊,刚想开口。 昂热已经系好了安全带,他透过车窗看着这三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尤其是他们那超载的交通工具,简洁地命令道: “别愣着了,上车吧。” 恺撒加图索最先动作。他利落地翻身下车,将头盔随意挂在车把上,动作间依旧带着加图索家特有的那种骄傲与优雅,尽管刚刚挤在摩托上的样子略显狼狈。他瞥了一眼那辆银光闪闪的宾利,又看了看驾驶座上神色平静的昂热,什么也没问,只是干脆地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将自己那双长腿在奢华的有限空间里安放好,目光平视前方,仿佛刚才风驰电掣、三人一车的窘迫从未发生。 楚子航紧随其后。他的动作更为沉默和利落,下车,将头盔递给还坐在摩托车后座、有点手忙脚乱的芬格尔,然后默不作声地拉开宾利后排的车门。 芬格尔是最后一个。他一边嘟囔着“哎哟喂可算能伸开腿了”,一边几乎是滚下了摩托车,差点没站稳。怀里还揣着路上买的零食,像个逃难的土拨鼠一样,哧溜一下钻进了宾利后排,挤在楚子航旁边。他长长舒了口气,好奇地摸了摸身下柔软的真皮座椅,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豪华升级感到十分满意,同时也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避免打扰到前面气场强大的校长和恺撒。 昂热没有再看他们,只是等所有人都上车、车门关好后,便干脆地启动引擎。宾利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平稳地驶入夜色中的街道,很快便消失在转弯处。 原地,只剩下艾伦威尔逊,以及那辆被遗弃的、看起来有些孤零零的杜卡迪摩托车。 艾伦脸上那公式化的、用于应对昂热和这个世界的公务员微笑,在宾利尾灯消失的瞬间,便如同被风吹散的薄雾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无所谓的平静,甚至带点空洞。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因为昂热强行开走他的爱车而恼怒,也没有因为那十倍的补偿而流露出真实的喜悦。 他抬手,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被昂热拽过的西装袖口,动作一丝不苟,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刺杀、对峙、交易、强行征用——都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随后,他转身,步态从容地准备离开。 然而,刚走出几步,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那段回住所的漫长步行路程,其现实的繁琐性,似乎比他刻意维持的“无所谓”姿态更具穿透力。他停下,像是忽然想起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再次折返,回到杜卡迪旁边。 他的目光精准地落在那空荡荡的钥匙孔上——钥匙果然已被拔走。一丝极淡的、预料之中的失望掠过他眼底,旋即消散。他对此并非没有准备。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这气息里带着一丝认命,但更多的是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步行,便步行吧。这个念头落下,他反而显得更加“安心”了,仿佛卸下了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侥幸。 官僚、牧师、乃至享乐主义者……这些不过是他根据需要披上的外衣,是应对不同人群和场合的面具。剥去这些,他内核深处所信奉的“上帝”,确实存在,却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神明。 那是端坐于无形王座之上的至尊,是注定要执掌这个世界运行法则的绝对君主。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行“必要之恶”,还是在官僚体系中周旋,亦或是此刻看似吃亏的妥协,最终都指向那唯一的、崇高的目的——服务于那位君主,铺平其执掌世界的道路。 一辆宾利,十倍车资,乃至一时的不便,在这宏大的图景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最后望了一眼昂热消失的方向,眼神深邃,没有任何情绪波澜,然后转身,步态从容地走向另一个方向,身影很快融入了夜晚的阴影之中,只有那辆杜卡迪摩托车就静静地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