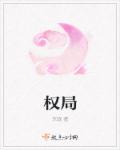剩套裤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彭成龙又在演州待了2天,跟伍氏道、陈顺、陈五郎、李正金、路夷等人聚在一起商议了今后“同乡会”发展、联系和保密的一些问题后,便满怀心事的赶回了西部元帅府; 毕竟,安南之战的成败跟他们关系也很大,一旦战败,他们的性命且不说,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也可能全部玩完,这不是彭成龙、张贤元等人愿意见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现在跟蒙元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当彭成龙回到西部元帅府把自己的分析跟文武们说了以后,果然从汪世显到西部元帅府的诸将、转运使、安抚使和长史、参军等都不太相信彭成龙的分析,别说主攻方向了,甚至对安南军是否会在雨季发动进攻都表示怀疑。 不过,汪世显也是用兵多年的人,虽然早年都在西北征战,但加入征南大军也有4年了,对安南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听了彭成龙的分析后,看了看安南的沙盘地形图,虽然对彭成龙说的主攻方向不太相信,但也认为安南军很可能在雨季发起全面进攻。 汪世显对现在的安南皇帝陈兴道、兴道王陈兴理、武义王陈国俊和陈兴道的太子陈光启这些人,他们的来历和能耐,都作过细致的打听,他知道这些人并非无能之辈,即便单独拿出来跟海都比,也都不差多少。 更重要的是,西北叛乱诸王中,只有海都一个人很厉害,而陈氏皇族,有雄才大略、善于用兵之人却有好几个,并且这些人还很团结。 当初元军能够一下打到升龙,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还有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后勤资源加持。 他忽然想起先帝的方略和现在朝廷的态度,摇了摇头,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先帝的方略,现在看起来,只能用穷兵黩武到极点来形容,完全是要把国家和百姓搞得杀鸡取卵一般,要求动员力度之大,后来的征海都都要相形见绌; 准备以60万大军(后续还有20万,共动员80万人马)、1200条船,水陆并进,一举弭平安南和占城,同时还要让真腊(高棉王国)和暹罗称臣(澜沧已经称臣),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开始决定征海都就已经动员得民怨沸腾了,再这样干,估计江山社稷能否保住都成问题,即便当年的秦皇汉武,也不敢这么想,更不敢这么干。 因此,正式决定征南时,先帝已经现实多了,只要求掌控红河平原粮食产地即可,大帝,在人力不能及之时,也只能认命,他也不敢逆天而行。 可是,也正因先帝迫不得已把征南的目的一再缩小,结果征南大军的兵员数额也一再削减,到最后,除了早先调来的十几万西北汉军,数万探马赤军和侍卫亲军,只动员了湖广、江西和云贵的七、八万衙役签军。 这些签军以老弱孺子为多,青壮都很少,就这样,湖广、江西和云贵已经是怨声载道,教匪盗贼蜂起了,到了终于决定发起南征行动的时候,只剩下22万人马还能用。 一年多来,大军顶着疾疫连续作战,在攻占升龙,扫平红河平原,臣服澜沧,一直进抵长山山脉并剿灭了安南北部各省的所谓“义军”后,大军已成了强弩之末。 即使在陈兴道发起新年攻势前,南部前线看起来兵力充足,其实也只能处于相持状态,若无增援和补充,想彻底平定安南实际已无可能,特别是水军撤出安南后,攻守之势更是逆转。 如今指望剩下不足15万的基本上全是陆上步骑的征南大军和傀儡黎朝所谓的10万“归元军”能全部守住粮食产地和北部运粮通道,已是难上加难。 可是,如果最后被赶出安南,不仅10万将士的血白流,而且先帝最小的目标都没有达到,失去了红河平原的粮食,难道继续维持在南方各省的高额粮赋吗。 征战多年,南方各省已被征粮征兵征赋搞得残破不堪,许多地方人口十不余一,喊了多年的减免赋税依然只是空话,别说许多早已沦为教匪盗贼的百姓了,南方原先归顺的乡绅大户,也是深感失望。 如果先帝仍在,绝不会容许安南成为第二个“南诏”,即使当时因为征西搞得天怒人怨,不得不缩小了征南的规模,但在海都平定后,必会将征西大军大部南调云南,谁想,先帝未及布置,便中道崩殂了。 唉,汪世显长长的叹了口气,他听说,此次越王能带着7万精锐前来增援,还是因为得到了太后和现今太子帖木儿的支持,否则,依今上多年来的表现,早就解散大军了。 7万增援精锐,在汪世显看来,也只能稳住当前形势,并夺回新年攻势失去的沱江路中南部、演州路南部、义安府路北部,但要想南下全占义安府路和新平府路,并最终攻占陈兴道的老巢顺化路,甚至趁势臣服占城,兵力远远不够。 关键是,新年攻势后,战略优势已经跑到安南人那边去了,想起新年攻势,这位带兵多年的宿将苦笑着摇了摇头,虽然越王千岁临上大都前,已经警告新年切勿放松戒备。 但是除了他要求将士们必须坚守驻地,不得休假,并四处打探消息外,东路和中路都是置若罔闻,中路主要是文官和越王亲信,兵力最少,主要职责是监视和训练所谓的黎朝和归元军,以及征收粮食,所以没做多少准备尚情有可原。 可是东路元帅府却在年前直接给那些蒙古和色目人放假,原因是东路大多数人认为,安南军已经大部被歼,剩下的早就吓破了胆,不足为虑,北方将士在此水土不服,将士思乡心切,应该准许将士们休假回乡探亲。 结果陈兴道发起新年攻势后,元军到处兵力不足,而那些北方探亲之人,有些现在还没回来。 还有主攻方向,因为千岁不在,这些人顾此失彼,吵得一塌糊涂,兵力一会调到这里,一会又驰援那里,搞得将士们疲惫不堪,结果是没给安南军造成多大损失,自己却失地还伤亡惨重,如果不是水军击败了安南水军,形势更是难以预料。 眼下,水军主力已经调往倭国,留下的寥寥无几,元军现在已经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7万增援力量的到来,估计也只能恢复战略平衡,想借此一举灭掉陈兴道,至少在汪世显看来,几乎不可能。 不过,汪世显并不清楚越王的计划,也不知道脱不花其实只带了2万人到安南,如果他知道脱不花的计划,不知道会怎么想。 眼下,没人怀疑陈兴道会再次发起进攻,问题是,何时,以及主攻在何地。 何时来攻,汪世显根据多年打仗的经验以及对陈氏家族的深入了解,完全赞同彭成龙的判断“雨季”,他惊奇的是,彭成龙了解的情况并不多,但却能做出这样宏观准确的判断; “果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汪世显心里这么想,对彭成龙又高看了一分。 陈兴道兵力有限,他会主攻哪里呢,本来根据汪世显在沙盘上的分析,安南军主攻南路是不太可能的,陈兴道占据西路战略位置这么关键的地方,而且在态势上占优(尽管元军在一再调兵增援西路后,此地目前元军兵力占优,但也仅此而已)。 只要安南人敢于加大投入,不说打下升龙,但至少切断北部粮道是完全可能的,毕竟,北部2路原先只有3、4万老弱签军,现在增援了东路元帅府的一半兵力,也就2万探马赤军和1万多侍卫亲军。 本来东路一开始进入安南就只有不到8万总兵力(其中汉军2万),连续作战,兵力已减至6万多,调了一半过来西路归化、宣光路,也未必就能久守; 若是安南集中10万...不,只要8万兵力,佯攻升龙,主力北上,完全有打破目前僵局的可能,一旦粮道被断,对整个征南大军意味着什么,汪世显都不敢想。 不过,或许陈兴道已经觉察到越王带着增援大军到来了,所以还想再等等,看看再说,但南路..汪世显走到沙盘前,皱着眉头仔细分析起来,他也知道元军水军撤走了,这么一看,似乎有那么点意思。 但他还是不敢相信陈兴道会这么干,舍近求远、舍本逐末,有这么用兵的吗,都不是傻子,陈兴道家族里的那些人,打仗都鬼精鬼精的,会这么干,但,如果是真的呢,他又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彭成龙。 彭成龙之所以这么笃定,还因为一个政治战略上的原因,安南虽然素来与占城交恶,但值此“唇亡齿寒”之时,占城定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陈兴道有求,只要胜利后能分得一杯羹,他们必定全力帮忙,而且,彭成龙还听说,占城的那个新王子,颇有胸怀和眼光,这至少说明,借水军的事,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汪世显是个老军人,显然不大懂这些政治战略上的事,即便他知道占城新王子很有才,也不会去想别的什么,但彭成龙这前世的销冠不一样,不仅本就是高材生,而且极善于观望形势和分析态势,虽然那是在商场,但商场就如战场啊。 汪世显本想先赞扬彭成龙对安南军进攻时机的预测,然后驳斥他关于主攻方向的判断,这既是自己的真实战争分析,又暗含恩威并施的意思,但想起彭成龙屡屡“算无遗策”,加上对水军撤离后南路形势的犹疑,他又不好这么做。 最终,汪世显决定把这个判断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那位年轻的千岁。 顺便,也看看你自己的本事,能不能把这个代领侍御史变成真正的侍御史,汪世显心想,随后,他拿起了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