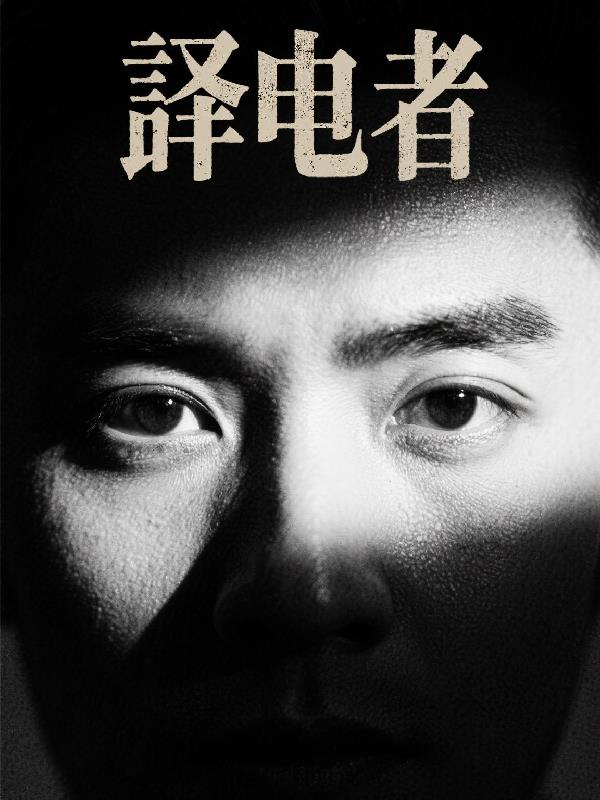第151章 立身存己
橙六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如懿未亲至永寿宫道贺,仅遣惢心代为一行。惢心形容枯槁,双颊深陷,眸中神采尽失,步履虚浮飘忽,显是魂不守舍。 她捧着一寻常锦匣入殿,对着魏嬿婉声气低微,勉力道:“奴婢代我家主儿,恭贺令妃娘娘晋封之喜。”语毕,便将锦匣奉上。匣中不过几朵色泽黯淡的旧式宫花,一方绣工平平的素色杭绸帕子,并一个半旧香囊,其中香料气息几已散尽。此等贺仪,敷衍寒酸,实难登大雅之堂。 惢心略顿,复又低低续言:“我家主儿特特吩咐奴婢转禀娘娘:娘娘您……向来奉皇后娘娘为……圭臬,最是仰慕中宫懿范高华,仁德昭彰。皇后娘娘素性简朴,不尚奢华,最重清净自持之风。想来……令妃娘娘既效皇后娘娘之贤德,克己复礼,亦必是……不喜虚华浮靡之物,唯重一片诚心。故而主儿才拣选了这些质朴无华的物件,虽……粗陋,却也……不敢悖逆皇后娘娘垂范,更合娘娘您素日崇尚俭德之心,望娘娘……莫要嫌弃……” 魏嬿婉面上波澜不惊,只略颔首,吩咐春婵:“惢心姑娘辛苦,看赏。” 春婵会意,取一把沉甸甸、金灿灿的金瓜子塞入惢心手中。惢心木然接了,神情恍惚,踉跄告退而去。 待其身影方没于殿外,侍立一旁的澜翠忍不住以帕掩口,嗤笑低语:“主儿方才赏她的金瓜子,怕是那匣中玩意儿全数变卖了,也抵不上一个零头!娴妃娘娘这手笔,啧啧……” 魏嬿婉莞尔道:“罢了。她此刻心中,怕已恨得银牙暗挫,强撑打发人走这一遭,已是折尽了颜面,此刻心里不定如何煎熬。这礼轻不轻的,倒也不必深究。” 正言语间,殿外王蟾躬身入内通传:“禀主儿,纯妃娘娘驾到。” 魏嬿婉忙敛容整衣,温声吩咐:“快请纯妃姐姐进来。” 苏绿筠移步入内,身着半旧的湖绿杭缎宫装,色泽沉暗,早失鲜亮,衬得人愈发气色灰败。昔日温婉秀美的容颜上,悄然添了几道细纹,眉宇间凝着一团化不开的郁结。最是那双曾含情带怯的美目,此刻眸光黯淡,浑如明珠蒙尘,透出深重的疲惫与无力。 魏嬿婉见其形容,心下暗叹,立时起身相迎,亲昵地执起苏绿筠微凉的手腕,引至窗下透气的湘妃榻旁落座,软语温言:“姐姐的心意,妹妹岂有不知这大暑天,日头毒辣,姐姐何苦亲自顶着酷热奔波遣个得力人来便是了,若中了暑气,妹妹心中如何安” 苏绿筠被她搀扶着坐下,唇瓣微颤,似有万语千言堵在喉间。忽地,她竟挣扎着又要起身,欲向魏嬿婉行大礼。魏嬿婉大惊,慌忙倾身,双手稳稳托住其臂,急道:“姐姐!姐姐这是为何万万不可行此大礼!折煞妹妹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快请安坐!” 苏绿筠被她牢牢搀住,身子微颤,抬起那双盛满哀恳与愧悔的眼眸,望着魏嬿婉,哀哀道:“令妃妹妹……从前是我糊涂,多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如今……只求妹妹……念在昔日情分,莫要……莫要与我计较前嫌……” 魏嬿婉心下了然,手上力道未松,只更轻柔地将苏绿筠按回榻上,眸光沉静如水,温声问道:“姐姐,那柄月琴……还在响吗” 苏绿筠闻言一怔,似未料她突然提及此物,眼中茫然一闪而过,正欲开口,却听魏嬿婉已续道:“我知道,姐姐所为,不过拳拳爱子之心,为母则刚罢了。只是……姐姐,我时常忆起在钟粹宫的那些夜晚,廊下风清月白,听姐姐纤指拂过冰弦,那琴音清越婉转,如珠玉落盘,又似幽泉咽石,是那样动人心魄,绕梁不绝。”她语声微顿,凝视苏绿筠瞬间苍白的脸,轻叹一声,“可自从端慧皇太子薨逝,姐姐便再未碰过那琴弦了。” 苏绿筠眼圈蓦地一红,喉头哽咽,半晌才低低道:“月琴……难为你……还记得。自从我叫可心收起来后,年深日久,琴在匣中久矣,连它收在何处……我……我竟也模糊不清了……” 她垂首以帕拭泪:“妹妹有所不知,这深宫之中,诸姐妹皆有根基凭仗。便如妹妹你,也是包衣出身,终究根基在彼。独我……出身寒微,不过是汉家平民女子,无门楣可依,论根基,如萍浮水;论才貌,更不敢望名门淑媛之项背。圣心重嫡重贵,论血统亲疏,我与膝下阿哥,实是…无有出头之日。” “我原是个没算计的,心思浅直,这宫闱之中千回百转的机窍,如何能转圜得过来不过只图守着本分,落个清净度日,日后但望阿哥得封个亲王,我们母子能享些安稳富贵,便是天大的造化了。” “可这宫里……何曾容得下不争不抢之人天家富贵,看似泼天,实则总有定数。人却似流水般,源源不绝地涌入这朱墙之内。人愈多,分润的恩宠便愈薄,不争……便唯有枯等零落!有阿哥傍身,总比膝下空虚者多一分倚靠。若……若自身无子嗣福泽,或子嗣不成大器,便唯有……令他人之子更不肖、更难长成……这宫闱倾轧,历来如此!我……我实在是怕煞了!”她双手紧紧攥着帕子,指节尽白,“我的永璋,我的永瑢……那是我的命根子,我的眼珠子啊!” 她仰起脸,泪光中满是绝望:“便是如今,皇上……都已有数月未曾驾临钟粹宫了……一旦再失了阿哥们的依傍……” “我在这重重宫阙之中,很快便会如尘埃般……被彻底遗忘……生生被锁在这四四方方的红墙黄瓦之内,日日唯有……数宫漏、看檐角日影西移,辨阶前草木荣枯……形影相吊,了此残生罢了……”语罢,已是泣不成声。 魏嬿婉并未即刻宽慰,她缓缓执起苏绿筠微凉的手,轻轻拍抚:“姐姐此言,道尽深宫妇人的无奈与惶恐,妹妹岂能不知然姐姐可知,妹妹心中最痛惜处,非在门楣根基之薄,亦非圣心恩宠之暂疏……妹妹痛惜者,是姐姐为那‘母亲’二字,竟渐渐失了‘自己’。” 此言一出,苏绿筠泪眼迷蒙,似有所触,却又茫然。 “昔年在钟粹宫,姐姐琴心独具,灵慧天成,是何等风致便是那账目繁杂,姐姐素日打理,亦是条分缕析,明明白白,我都看在眼里。彼时的姐姐,顾盼间自有光华流转,令人见之忘俗。” “可为了阿哥,姐姐眼中、心中,便只余下‘皇子之母’四字,再无其他。面圣之时,姐姐言必称阿哥学业、起居、前程……渐渐地,姐姐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只为阿哥存在的‘牌位’。月琴久置蒙尘,算盘珠网暗结,姐姐浑然不觉。姐姐将一身光华、才情、乃至灵性,尽数倾注于阿哥之身,仿佛唯此,方显为母之诚。姐姐,此非爱子,实为…戕己!” “姐姐方才言道,无子嗣者,或子嗣不成器者,便要设法令他人子嗣更不成器、更难长成……姐姐啊,姐姐今日为保阿哥,惶惶不可终日,岂非正因姐姐早已将己身全然依附于阿哥之上姐姐失了根骨,失了自持,失了那份‘我之为我’的立身之本,故觉风雨飘摇,无所依凭。” “人立于世,贵在自重。若连己身都看轻了、舍弃了、湮没了,纵有千般倚仗,终不过无根之萍,无本之木。风浪来时,如何能立姐姐的月琴、算筹、灵慧才情,那才是姐姐自身的光华!此光华若在,纵使圣心难测,阿哥前程未卜,姐姐依旧是那独一无二、令人不敢轻慢的苏绿筠。此光华若黯,纵使阿哥尊荣无限,姐姐亦不过是依附其侧的一道虚影罢了。而虚影,正是极易被这深宫的红尘…彻底湮灭的。” 言罢,魏嬿婉抬手,细细替她拂去眼角泪痕:“妹妹今日之言,句句肺腑。望姐姐细思,莫再为保‘皇子之母’的虚名,而彻底磨灭了‘苏绿筠’这个人。人先自敬,而后人恒敬之。这,方是真正的立身之道,亦是保全阿哥的长久之计。” 苏绿筠闻之,更是泪涌如泉,身子一软,竟从座上滑落,斜倚魏嬿婉身前,双手紧攥其袖,呜咽难休:“妹妹……妹妹啊!你今日这番话,字字如针,扎在我心坎上!这深宫之中,谁还记得‘苏绿筠’素日爱些什么擅些什么人人只道我爱儿成痴,便是我自己……我自己也早已视儿如命!那些琴棋书画、料理庶务的本事,那些曾让我心头欢喜、指尖生香的玩意儿……为了孩儿,皆可抛却!皆可……灰飞烟灭!” “妹妹肺腑之言,姐姐感念至深……可……可姐姐怕是真的做不到了……再做不到了啊!这惶惶不可终日之心,如附骨之疽,日夜啃噬,教我如何挣脱如何寻回那旧日的‘自己’我怕……怕极了……” 魏嬿婉俯身,着力将她复又搀起:“姐姐,你最大的症结,便是这耳根子忒软了!旁人几句危言耸听,几句捕风捉影,便能搅得你心胆俱裂,失了方寸。这‘耳根子软’四字,在寻常人家,或只落个糊涂名声;可在这步步荆棘、处处深渊的深宫里头,便是害人害己的穿肠毒药!” “你既自知谋算不如人,家世根基又浅薄无依,那就更该明白一个道理:那些显赫门第的,纵有起落浮沉,到底有祖宗荫庇、家族托底,便是跌倒了,也还有爬起来的气力与凭仗。姐姐你呢一次行差踏错,一次被卷入无谓的漩涡,便可能是万劫不复!你并无那起死回生的‘托底’之力啊!” “如此境况之下,姐姐尤要谨而慎之。‘少听’——不听那些搬弄是非、搅乱人心之言;‘少言’——不妄议宫闱,不轻泄心事。这便是你最大的护身符!远胜过费尽心思去依附哪个,以求那虚无缥缈的‘荫蔽’!” “再者,依附他人,便是将身家性命悬于他人股掌之上,那人自身尚且风雨飘摇,又能荫蔽你几时一旦大厦倾颓,依附者便是最先粉身碎骨的瓦砾!” 苏绿筠眼中强自浮起一丝恍悟之色,她身子前倾,双手骤然紧攥魏嬿婉腕子,切切道:“妹妹,我明白了!当真明白了!从今往后,姐姐定当洗心革面,安守本分,只当自己是那眼瞎耳聋的木头人!这宫闱风云、闲言碎语,我一概不知不问!只求……只求妹妹……妹妹你……再不计较了罢” 魏嬿婉心下轻叹。苏绿筠这性子,软弱已入骨髓,心魔既种,便如附骨之疽,非言语药石可拔。今日这番剖心沥胆之诫,只怕是春风过驴耳,一字未曾真正敲进她心里去。苏绿筠只道是告诫她莫争宠、莫生事,却全然不解那‘立身存己’方是根本。她所求的‘宽宥’与‘不计较’,不过希冀得一个“不究既往”的承诺,好能蜷缩于那“眼瞎耳聋”的硬壳中,依旧盼望着阿哥,惶惶度日。 罢。 魏嬿婉缓缓将手自苏绿筠掌握中抽出:“是了,姐姐。只要你安守本分,谨记今日之言,老实度日,我自不会如何。” 苏绿筠所求之‘不计较’,她自可予之;然苏绿筠真正需索之‘立身之道’,她却是无心亦无力强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