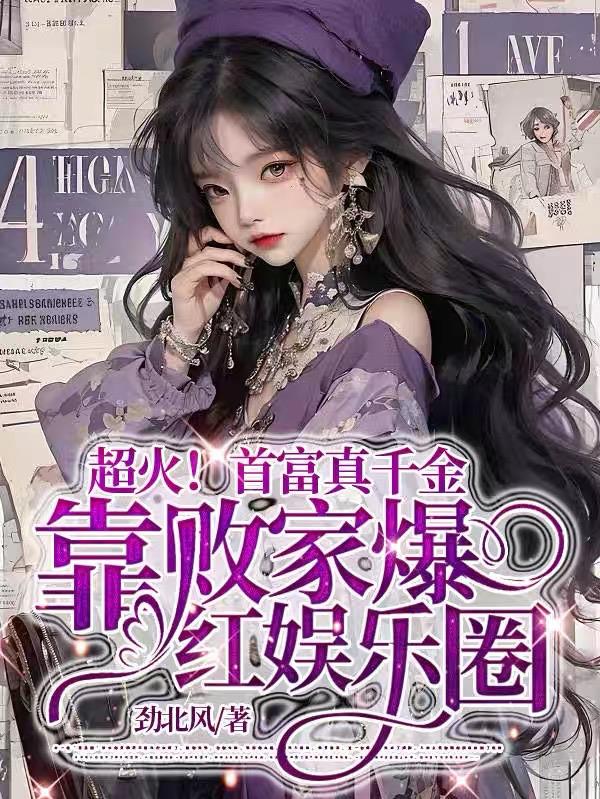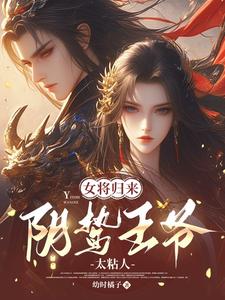第275章 江澈的难题,没钱怎么盖楼?
书魂栖玉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夜深了。 市政府大楼的灯一盏盏熄灭,像一只只疲惫的眼睛缓缓闭上。唯有江澈办公室的落地窗,还在不夜的城市灯火中,亮着一小片孤独的光晕。 周源已经走了,走的时候,眼神里混杂着崇拜、激动和一丝担忧,像个即将目送将军出征的小兵。 江澈没理会他复杂的内心戏。他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那份关于三大家族的详细资料。桌上的台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背后的墙壁上,像一尊沉默的思考者雕塑。 他没有思考。 他在发呆。 脑海里,那个穿着海绵宝宝睡裤的小人,正盘腿坐在一堆由“财政赤字”、“刚性支出”、“重点项目”等字样堆砌成的大山前,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塑料铲子,一脸茫然。 怎么挖 这山,根本就不是土做的,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上面还贴着“合规”、“合法”、“按流程办事”的光滑瓷砖,连个下手的地方都没有。 常规的路子,已经被他自己亲手堵死了。 今天下午在财政局那番“交锋”,看似是他占了上风,用一个尖锐的问题将了王建国一军,让对方颜面扫地。但江澈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一场表演。一场演给所有人看的、名为“我已经尽力了”的独角戏。 他把正门堵死了,才好方便自己,去翻那扇早就看好的窗户。 【叮!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自我pua”式复盘,并成功将“走投无路”的被动处境,美化为“深思熟虑”的主动布局。】 【系统评价:恭喜宿主,“官场老油条”心态已臻化境。您的脸皮厚度,已超越本市99.9%的同级别干部。】 江澈对系统的嘲讽置若罔闻。他的目光,重新落回桌上的文件。 手指在李家那份“文化旅游配套商业用地”的补充协议上轻轻敲击着,发出沉闷的“笃、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如同秒针在倒数。 这块地,是他的第一个突破口。 但一个突破口,还不够。 他要的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那太费劲,后患无穷。他需要的是一场优雅的、所有参与者都面带微笑的“集体募捐”。他要让这些铁公鸡,不仅要拔毛,还得自己把毛洗干净、捆成一束、微笑着递到他手上,并由衷地说一句:“江市长,您辛苦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这,才叫艺术。 江澈的视线,从李家的文件,缓缓移到了旁边张家和王家的卷宗上。 上一世在省厅核心处室,他见过太多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看似独立的个体,实则早已通过各种项目合作、联姻、共同的利益诉求,编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 他拿起笔,开始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画线。 张家的“四海集团”,在老城改造中,主要负责的是古建筑的修缮工程。他们以“采用古法工艺、传承非遗技术”为名,申请了一大笔专项补贴和税务减免。但卷宗的附件里,一份不起眼的第三方审计报告指出,其主要的材料供应商,是一家去年才成立的“古韵建材公司”,注册地址就在四海集团总部的隔壁楼,法人代表,是张家老爷子司机的表外甥。 王家的“金鼎置业”,则拿下了老城改造区域内所有新建基础设施的水泥供应。他们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出近三成,理由是采用了“专为保护历史风貌区地下管网而研发的特种水泥”。而这份“特种水泥”的专利持有者,恰好是王家二公子在国外注册的一家离岸公司。 李家的地,张家的补贴,王家的水泥。 三条看似不相干的线,在江澈的笔下,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交点——老城改造项目总指挥部。而当时的总指挥,正是如今的市长,赵立春。 当然,江澈百分之百确信,以赵立春的精明和爱惜羽毛的程度,他绝对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勾当。但作为总指挥,项目里出现了这么大的利润黑洞,他不可能毫不知情。他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交换。他需要这些本土势力在拆迁和改造过程中“配合”,而这些,就是他默许的“补偿”。 水至清则无鱼。 江澈的嘴角,勾起一个无人察觉的弧度。 他终于找到了那把能撬动所有人的钥匙。 他要做的,不是去揭发谁,更不是去威胁谁。他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局”,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无法拒绝的局。 在这个局里,赵立春需要一个机会,来堵上老城改造留下的那个小小的、可能会影响他未来仕途的“程序瑕疵”,将一桩潜在的麻烦,变成一笔光彩的政绩。 三大家族也需要一个机会,来“洗白”他们那些不太干净的利润,花小钱,买心安,顺便在市长面前,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名声。 而聋哑学校的孩子们,需要钱,来盖一栋新校舍。 他,江澈,只需要把所有人的需求,打包在一起,然后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必须有一个华丽的、充满正能量的舞台。 它不能是一场分赃会,而应该是一场慈善晚宴。 它不能是一次勒索,而应该是一次“爱的奉献”。 江澈靠在椅背上,缓缓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无数个方案碎片开始飞速碰撞、拼接、组合。 一个完整的计划,像一幅精密的建筑蓝图,在他的脑中逐渐清晰。 第一步,造势。 他不能自己去哭穷,说学校多可怜,政府多没钱。那样格调太低,而且会把财政局和市政府架在火上烤。他需要一个“第三方”,一个有公信力、有影响力的声音,来把这个故事,讲给全云州的人听。 第二步,搭台。 他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把所有关键人物都请到同一个场合。这个场合,不能太官方,否则会显得像一场鸿门宴;也不能太随意,否则会显得不够郑重。 第三步,唱戏。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道具”,来确保台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按照他写的剧本,念出他想要的台词。 江澈睁开眼,那双深邃的眸子里,已经没有了半分慵懒和疲惫,只剩下一片算计之后的清明。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没有打给周源,也没有打给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他翻开自己的私人电话本,找到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 电话“嘟”了几声后被接通,一个苍老而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喂,你好。” “陈教授,您好,我是江澈。” 电话那头,是云州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陈望年。一位在云州文化界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老学者。江澈在搞老城改造的时候,曾多次向他请教,相谈甚欢。 “哦!是小江市长啊!”陈望年显然还记得他,声音里透着一丝惊喜,“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个老头子打电话了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历史难题了” “难题倒是有一个,但不是历史方面的。”江澈笑了笑,语气放得十分轻松,“陈教授,我是想向您请教一个关于‘慈善’的问题。” “慈善”陈望年有些意外。 “是啊,”江澈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闲聊,“我今天去了一趟市里的聋哑学校,感触很深。我就在想,咱们云州历史上,有没有那种乡贤名流,捐资助学、造福乡里的传统和佳话” 陈望年一听这个,立刻来了精神,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哎呀,那可太多了!咱们云州自古文风昌盛,明清两代,出过好几位大商人,发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修桥、铺路、建义学!最有名的,当属清末的‘布业大王’李善堂,他一个人,就捐建了三所蒙学,让多少穷人家的孩子有书念啊!他的那句‘积财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德于乡里,福泽可延百年’,至今还在我们李氏宗祠的牌匾上挂着呢!” 江澈安静地听着,听到“李氏宗祠”四个字时,眼中的光芒微微一闪。 “陈教授,您说的这些故事,太感人了。可惜啊,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恐怕不多了。”江澈故作惋惜地叹了口气,“这么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是能让更多人知道,该多好。” 电话那头的陈望年,立刻被勾起了共鸣,声音也高了几分:“是啊!谁说不是呢!现在的社会,都盯着钱看,这种古道热肠,越来越少了!小江市长,你今天提的这个话头好啊!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宣传!让现在这些赚了大钱的企业家们,都跟老祖宗学学!” 江澈要的就是这句话。 “陈教授,我就是这么想的。您是咱们云州文化界的泰山北斗,您要是能牵个头,比如,在咱们市电视台的文化栏目,或者在《云州日报》上,写几篇文章,搞一个‘云州乡贤慈善故事’的系列专题,那效果肯定不一样。”江澈不着痕迹地把球踢了过去。 陈望年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下来:“这个好!这个我义不容辞!我明天就联系报社和电视台!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那就太感谢您了,陈教授。我代表那些孩子们,谢谢您。” “谢我干什么,这是我该做的!” 挂了电话,江澈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一步,成了。 可以预见,从明天开始,一股关于“慈善传统”、“乡贤责任”的舆论暖风,将在陈望年教授这位“意见领袖”的引领下,吹遍云州的大街小巷。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为富须仁”的道德氛围中时,他再搭台唱戏,就顺理成章了。 江澈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是云州璀璨的夜景。车流像金色的河,在高楼的峡谷间静静流淌。 他看着这座城市,心中那个穿着海绵宝宝睡裤的小人,不知何时,已经爬上了那座由“困难”堆砌成的大山顶上。 小人没有欢呼,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望远镜,望向了更远的地方。 在那片黑暗的尽头,似乎还有更高、更险峻的山峰,在等着他。 他收回目光,拿起外套,关掉了办公室的灯。 该下班了。 明天,还有一场好戏,等着他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