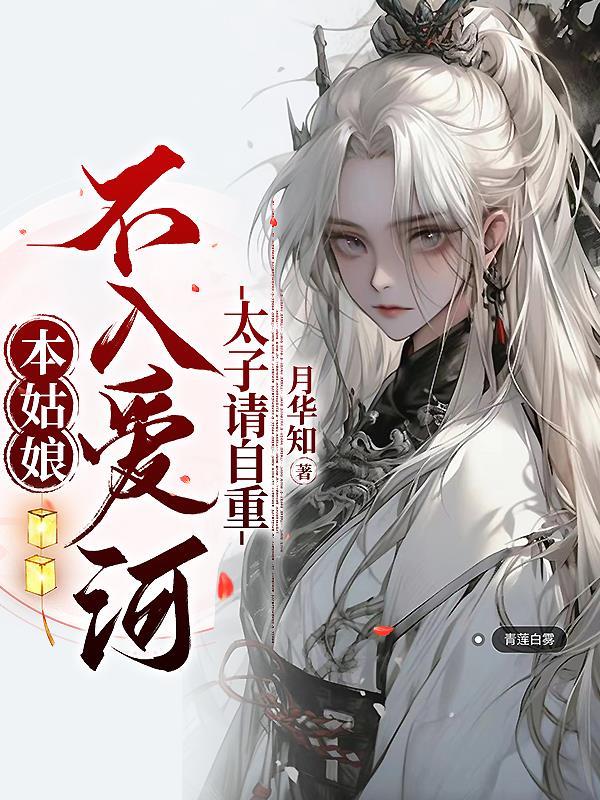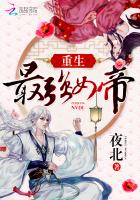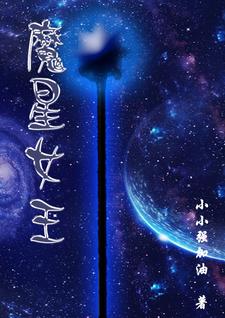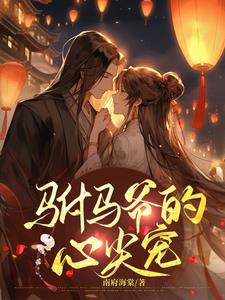稿纸种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一日。 林昭然整日未曾踏出米行半步。 长安城里的风声鹤唳,似乎都与这间小小的后院无关。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窗下,日光透过窗棂,在她素净的衣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碎金洒落,又似时光缓缓爬行。 蝉鸣在院角的老槐树上断续响起,远处市井的叫卖声被高墙隔成模糊的余响,唯有风拂过纸窗的窸窣,与她指尖轻叩桌面的节奏应和着。 柳明漪捧着一本重新装订过的《蒙学新编》走进来,书的封面被刻意做旧,纸页泛黄,边角磨损,仿佛是哪位前朝大儒不经意间遗落的稿本。 她脚步微滞,裙裾擦过青砖,带起一丝凉意。 “公子,都照您的吩咐弄好了。”柳明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喉间微动,像是咽下了未尽之言,“真要这么做吗万一……” 林昭然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打断了她的担忧:“没有万一。”她接过书,指尖触到那粗糙的纸面,微涩而温厚。 她小心翼翼地翻开,将七枚擦得锃亮的铜钱逐一夹入书页之间。 每翻一页,纸张发出极轻的“簌”声,铜钱落定,发出细微的“叮”响,像是命运落子的轻音。 每一枚铜钱上,都用细不可查的刻刀,精心雕琢了一个字。 连起来,便是“三日不见如隔三秋”。 “国子监的书役处,收录杂书遗稿,向来只登记书名,从不细翻内容。你把它送去,就说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孤本,请他们归架即可。”林昭然将书递回给柳明漪,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家事,指尖在书脊上轻轻一抚,仿佛送别一个沉默的信使,“监生们大多家境优渥,但也总有那么些好奇心重、又爱寻章摘句的。一本从未见过的‘遗稿’,足以勾起他们的兴趣。” 柳明漪用力点了点头,将书揣入怀中,转身快步离去。 她的脚步踏在青石板上,渐行渐远,最终隐入巷口的薄暮。 林昭然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重新坐回窗前,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木纹的凉意透过指腹渗入心间。 她不担心书会不会被发现,只担心发现得够不够快。 她要的,不是石沉大海,而是一圈恰到好处的涟漪。 果不其然,当晚,消息便顺着陈砚秋的渠道传了回来。 国子监里几个素来喜欢猎奇的监生,在书库角落里翻出了这本所谓的“旧书遗稿”。 书库中尘埃浮动,油灯昏黄,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有人翻开书页,铜钱滑落,发出清脆的“当啷”一声,引得众人侧目。 “三日不见如隔三秋”有人将那七枚铜钱在桌上一字排开,念出声来,引得众人一阵哄笑,笑声在梁柱间回荡,“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借书传情,暗诉相思呢” “这字刻得倒是精巧,也不知是哪位仁兄的艳福。” 他们笑谈着,将这事当成了一桩风流趣闻,在相熟的同窗间传扬开来。 无人深思,也无人警觉,只觉得这桩投帖风波里,又多了一丝香艳的点缀。 他们更不会知道,那看似缠绵的“三秋”,正无声地倒数着一个冷硬的期限。 这悄然布下的引线,已将所有人的目光,都牢牢牵引到了三日之后,她林昭然的投帖命运之上。 第二日,天色微明。 国子监补经班的讲堂里,气氛有些沉闷。 晨光透过雕花窗格斜照进来,映在青砖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监生们大多心不在焉,三三两两地低声议论着林昭然投帖之事,语声如蝇,夹杂着笔杆轻敲砚台的“嗒嗒”声。 陈砚秋一袭青衫,走上讲台,面色一如既往的温和,眼神却比平日里多了几分锐利。 他没有理会堂下的窃窃私语,只是翻开书卷,朗声道:“今日,我们讲《孟子告子上》。” 他的声音清朗,穿透了讲堂的嘈杂:“‘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他念完,并未像往常一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经义,而是抬起头,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位监生的脸。 有人低头避视,有人皱眉沉思,有人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笔。 “诸位,”他沉声开口,语气陡然变得严肃,“孟子此言,论的是教化之道,亦是存亡之道。再容易生长的东西,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也绝无可能存活。我大周开科取士,广纳贤才,正是为了培育教化之苗,使天下文风蔚然。可如今,国子监门前,有一株好苗,只因其出身,便要拒之门外。” 堂下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都仿佛被压低。 窗外的风掠过檐角铜铃,发出一声悠远的轻响。 陈砚秋的声音愈发激昂:“诸位可知,国子监拒一人,非拒一人,实乃拒绝天下寒士之望!今日晒之以期,明日寒之以拒。若三日寒之,十年暴之,试问,我大周的教化之苗,将来何以丛生天下士子的向学之心,又将置于何地” 一番话掷地有声,如巨石投湖,激起千层浪。 监生们面面相觑,脸上的散漫与轻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沉思。 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出身富贵,但也自诩为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骨与骄傲。 陈砚秋的话,恰恰击中了他们内心最柔软也最敏感的地方。 见火候已到,陈砚秋从袖中取出一沓早已备好的信纸与笔墨,分发下去。 有人接过纸时指尖微颤,有人低头凝视空白纸面,仿佛在称量笔墨的重量。 “课毕,请诸位各写一信,题为《致国子监书》。不必署名,只在信末写上一句话便可。”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若林昭不得入,我辈虽在监中,亦如在外。” 笔墨落在纸上的沙沙声,在寂静的讲堂里汇成了一股沉默而坚定的洪流。 墨香淡淡弥漫,混着晨露的湿气,沁入人心。 第三日清晨,大雨初歇。 太学博士赵元度如常来到讲堂准备讲经,却发现自己平日里整洁的讲案上,竟堆起了小山一样高的信件。 他眉头微蹙,指尖触到信纸,尚带着昨夜的潮气。 随手拿起一封拆开,纸页发出轻微的“刺啦”声。 信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刚劲有力的字:“若林昭不得入,我辈虽在监中,亦如在外。” 他愣了一下,又接连拆开数封,内容竟完全一样。 他的脸色由疑惑转为严肃,再由严肃转为阴沉。 他没有再讲经,而是抱着那一叠沉甸甸的信,径直闯入了礼部衙署。 裴仲禹正在堂中处理公务,见赵元度怒气冲冲地进来,不由得皱起了眉。 “元度兄,何事如此失态” 赵元度将那叠信重重地拍在裴仲禹的案上,声若洪钟:“裴侍郎!三日之期未到,国子监的人心,已经快要失尽了!” 裴仲禹拿起一封信看了看,冷哼一声:“一群黄口小儿的胡闹罢了,何来人心之说” “胡闹”赵元度气极反笑,“你可知这些信有多少封七十二封!这还只是补经班!若黜落林昭,我们失去的,绝不止一个林昭,而是天下士子对朝廷法度、对国子监的信任!是失天下士心!” 裴仲禹脸色铁青,强硬道:“投帖程序尚未走完,何谈黜落一切按规矩办!” “规矩”赵元度上前一步,紧盯着他的眼睛,“若所谓的规矩,只是为了拖延与搪塞,你以为人心会自欺欺人吗他们会看不出来吗” 他不再多言,留下一句“好自为之”,便拂袖而去。 裴仲禹独自站在堂中,胸口剧烈起伏。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信纸的一角,似乎还有另一行墨迹稍淡的小字。 他凑近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昔拒一林昭,今失百林昭。” 那一瞬间,他握着信纸的手,竟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一直侍立在侧的礼部主事周砚修见状,连忙上前,低声劝道:“侍郎大人,下官看这林昭,其心可畏。她不求速成,而求众信。三日之内,环环相扣,竟让国子监的监生们都以为这番抗争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而非受人鼓动。此子,智计非凡,若强硬拒之,恐激起更大风波。” 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建议:“依下官愚见,堵不如疏。不如假意允其入学,给他一个‘试读’的名分。如此,既全了程序,安抚了监生,又可将他置于我们眼皮底下。监内规矩森严,她行事稍有不慎,我们便可名正言顺地将其黜落,永绝后患。” 裴仲禹沉默了许久,眼中的怒火渐渐被一丝阴冷的算计所取代。 他缓缓走到案前,提起笔,在一份文书上写下批示:“准录。试读三月,以考校其心性德行。” 笔锋落下,他发出一声冷笑:“我倒要看看,让他进来,他要如何自己滚出去!” 消息很快传回了米行。 陈砚秋几乎是跑着冲进后院的,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昭然!你赢了!裴仲禹批了!试读三月!” 林昭然却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她将手中的《论语》残卷翻到“君子不器”那一页,指尖轻轻抚过那四个字,纸面粗糙,墨痕微凸,仿佛刻着千年的重量。 “不是赢,”她轻声说,“是他们,终于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度了。” 她抬起眼,看向陈砚秋,目光深远而透彻:“他们以为,给我一个随时可以收回的试读身份,就能将我困于牢笼,驯化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可他们错了。” 她合上书卷,站起身。 “我要的,从来都不是国子监里的一张席位,而是要改一改这套只为权贵服务的规矩。” 她转向柳明漪,声音清亮而果决:“去准备监生青衫。明日,我将以‘试读监生林昭’之名,正式入监。” 当夜,紫宸殿侧阁。 沈砚之就着一盏孤灯,翻阅着今日从各部呈上来的简报。 烛火在他冷峻的侧脸上跳动,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 当他看到关于“林昭投帖”一事的宗卷时,动作停了下来。 宗卷之后,还附着那七十余封《致国子监书》的誊抄本。 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内容,最终落在了宗卷开头,关于那本《蒙学新编》的记载上。 “三日不见,如隔三秋。” 他指尖抚过这八个字,墨黑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恍惚。 这句子,何其眼熟。 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是多年前,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在长安城外一座破庙的墙壁上,用石子刻下的戏言。 后来,那座庙和他曾经的路,都一同被他亲手烧毁在了一场大火里。 他沉默良久,提起朱笔,在宗卷末尾裴仲禹那句“考校心性”的批文旁,轻轻落下了三个字。 “三日,不够。” 写完,他放下笔,合上宗卷,目光投向窗外。 长安的夜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琉璃瓦,也敲打着沉寂的宫城。 夜色深沉,雨声渐歇。 黎明前的寂静,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国子监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在晨光熹微中,像一只沉默的巨兽,等待着那个即将叩响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