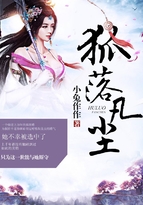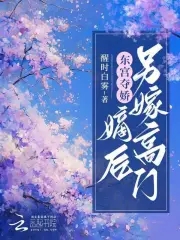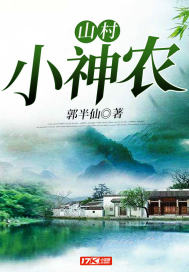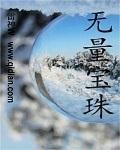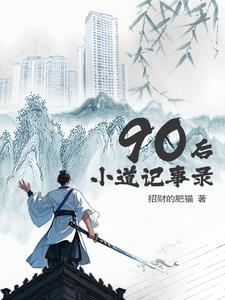小咪的衣食父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北大窑改了名字叫盘山砖厂。 耸立的烟囱每日都冒着滚滚浓烟,像一支铁灰色的巨笔,在蔚蓝的天空写下浓墨重彩的图画。 那烟不是乌沉沉的死灰,而是一团团被炉火舔得通亮的云,卷着火星子往天上冲。远远望去,像一条挣脱了束缚的赤龙,在风里翻腾,把盘山城里城外的寒气都逼退了三分。 风里裹着的硫磺味儿掠过砖窑,窑口的火光将傍晚的云霞染得愈发炽烈,刚出窑的红砖泛着青黑色的光泽,被铁板的滚床运出来时,还带着灼人的热气。 德麟站在窑顶的了望台,一身粗布夹袄被烤得发脆,袖口沾着红土,脸上映着火光。他抬手抹了把汗,指缝里都嵌着细细的红砖末。 厂区里穿梭的板车,正排着队把刚出窑的红砖运出去。红砖码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像列队的新兵。 砖缝里透出的余温,把赶车汉子的眉毛都烘得卷了起来。车辙压过的盐碱地上,碾出深深的沟壑。 砖厂的操场上,一台台的拖拉机排着队,等着工人们把一垛垛红砖装上后车斗。“突突突”地吼叫着,把热乎乎的红砖,送往盘山农场各处的建筑工地。 “再跑一趟!城北的粮库今儿得封顶!”德麟的嗓子沙哑,却掩不住笑。 他一笑,眼角的褶子就挤出两枚浅浅的月牙,像砖坯上不小心按下的指纹。 砖厂的活计又苦又累,可苦里累里也蓄满了甜。 几年前这儿还只是一片荒窑,德麟领着十几号人,用铁锹、箩筐和肩膀,硬生生把窑口挖开,重新改了里面的构造。上了最新的机器设备,把土和成泥,把泥烧成砖。 如今,盘山城墙根下的豁口、被洪水啃噬的堤岸、炸成麻花状的铁桥,全靠这一车又一车的红砖慢慢缝补起来。 还有整个盘山县城变农场的重建。城东的供销社刚起了地基,盘山小学的教室正在上梁,连农场大院的围墙都用着这里烧出的红砖。 夜里,德麟常独自蹲在窑后,听火舌舔砖的哔啵声,觉得那声音像自己胸腔里跳着的另一颗心。 他粗糙的手掌抚过了望台的铁栏,栏杆上还留着经年累月的温度,这双手曾无数次伸进窑口探查火候,指节上结着厚厚的茧子,虎口处还有被火星烫出的疤痕。 “夏厂长,这批砖硬度够!农场工地的李工头说还要加订两车。”烧窑师傅老张隔着窑道喊,声音被热浪烘得有些发飘。 德麟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里落满了烟灰。 三年前砖厂刚投产时,他带着五十多个工人没日没夜地守在窑边,第一批砖出窑,硬度不够,烧裂了一半,他蹲在废墟里盯着碎砖看了整夜。 第二天就带着人翻修窑体,把老祖宗传下的烧窑口诀写在烟盒纸上,反复琢磨火候与风压的关系。 机器卡了,请不来厂家的技术工程师。德麟没日没夜的啃书本,做实操,一遍遍打电话请教,硬是自己琢磨透了。 如今砖厂日产红砖五千块,不仅解了县城重建的燃眉之急,还让一百多个村民有了稳定的活计。 可就在窑火最旺的当口,一纸政令下到盘山农场,村子要改制成生产队。 砖厂的烟囱熏黑了天边的云霞,笼罩着夏家村的土墙上贴出的大红告示。根据盘山农场指示,夏家村正式改制为夏家大队,要选队长。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天就传遍了十八个自然村。 村委会的老槐树下挤满了人,竹椅上的老人吧嗒着旱烟,年轻媳妇抱着孩子议论纷纷。 “我看老夏家的德麟行,”村东头的王铁匠磕了磕烟锅,“砖厂都被他盘活了,咱大队交给他准没错。” 这话像投入湖面的石子,立刻激起一片附和。有人说德麟为人实诚,去年闹春旱,他把砖厂的抽水机让给村里浇麦田;有人说他脑子活,懂得算细账,不像有些干部光会喊口号。 当村民代表把推选结果送到德麟手上时,他正在砖厂的记账本上核对数字。泛黄的纸页上记着每窑砖的数量、耗煤量,字迹工整得像砖缝排列的纹路。 “这……”他捏着那张盖着红手印的推选表,指腹摩挲着村民们歪歪扭扭的签名,心里像压了块刚出窑的红砖,沉甸甸的。 傍晚时分,盘山农场的场长兼主任韩庆年骑着旧自行车,来找德麟。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人民服,裤脚沾着泥点,显然是从村里一路骑过来的。 “德麟,”他拍着德麟的肩膀,手掌的力度比往常重了些,“你是省里都挂号的人,都知道你的本事,可这生产队的担子......” 德麟见他欲言又止,憨厚地笑了,眼角的纹路里还沾着窑灰:“韩场长,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他知道韩庆年的顾虑,砖厂刚步入正轨,正是需要主心骨的时候,可生产队刚刚改制,百废待兴,更离不开能挑大梁的人。 韩庆年看着他被烟火熏成深褐色的脸颊,突然松了口气,又有些愧疚。 那年冬天砖厂缺煤,是德麟带着人去一百多公里的抚顺煤矿拉煤,用的是砖厂自己的拖拉机。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却笑着说“砖不能停”。 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 砖厂的事刚交割完,更大的浪头打来了。 大跃进的风带着特殊的热度吹遍了全国。 广播匣子里天天喊着“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口号贴满了盘山城的墙壁。 城里竖起一座座小高炉,像雨后冒出的毒蘑菇。 年轻人揣着进城当工人的梦想涌向城里。他们挤在卡车后斗里,唱着歌往城里涌。 德麟却卷着铺盖从场部,住进了夏家大队的队部。 夏家大队的青壮年走了大半,连村小学的教书先生都辞职,去了农场里的钢铁厂。 德麟站在村口,看着那些曾经一起掏鸟窝、滚铁环的伙伴,如今穿着劳动布工装,胸口别着搪瓷厂徽,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夜里,他躺在队部冰凉的土炕上,听窗外北风卷着铁哨般的尖啸。 炕桌上摊着一本账簿,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可数字总对不上。缺人,缺劳力,更缺能写会算的人。 站在队部的门口,望着空荡荡的晒谷场,德麟的心里像被秋风吹过的田野,空落落的。 生产队要记账、要统计工分、要核算粮食产量,没有个懂文墨的人可不行。 他在煤油灯下翻着通讯录,手指停在“德昇”两个字上。 弟弟德昇高小毕业,考上了技校,念了两年半。又考上了鞍山钢铁学院,去年“学生变工人”,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农场,算算日子,已经快两年没回家了。 德麟立刻铺开信纸,给德昇写信叫他回来。 信写了改,改了又写,直到窗纸泛起鱼肚白才封好。他在信里没说自己的难处,只说“弟:见字如晤。如今大队缺会计,盼你归来。兄不才,愿与你并肩。——兄德麟。” 信投进邮筒那天,德麟在村口站了半晌。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怕村里的老老少少吃不上高粱米饭,又怕耽误了弟弟的前程。 日子在掰着指头的等待中流逝。每天收工后,德麟总要绕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通往县城的土路尽头。 队里的账越来越乱,有社员开始嘀咕:“没个正经会计,这日子咋过” 他听着这些话,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己趴在炕桌上,一笔一笔计算,核对,煤油灯一亮就又亮到天明。 第二十天傍晚,德麟刚把最后一头牛赶进牛棚,就听见村口传来孩子们的叫嚷:“德昇哥回来啦!” 他心里一紧,抄起搭在墙上的草帽就往村口跑。 夕阳把土路染成金红色,远处两个身影正慢慢走近。 走在前面的是德昇,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帆布包沉甸甸地挂在肩上。晒黑的脸上带着风尘,看见他时,眼睛亮了亮,脚步也加快了些。 而跟在德昇身后的,竟是老父亲夏三爷。 从黑龙江到盘山农场,他们徒步走了两天的路,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 夏三爷的眉头,一路没松开过。车厢里,烟丝的味道混着尘土味,成了德昇记忆里归途的气息。 “你哥在砖厂时就护着你,”三爷嘱咐,“没有公家,你能念这么多年的书现在生产队需要你了,你们兄弟俩得搭好伙。” “哥。”德昇走到德麟近前,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稳稳的底气。 德麟望着弟弟眼里的红血丝,又看了看他帆布包露出的半截书本,喉咙突然发紧。 他想说句辛苦,想问问学业,最终却只化作一句:“回来就好,家里的炕给你烧暖了。” 晚风穿过老槐树的枝叶,带着苞米秸秆的清香。德昇把帆布包往肩上紧了紧,笑着说:“哥,明天我就去大队部理账,咱兄弟俩一起把队里的生产搞起来。” 德麟望着弟弟年轻却坚定的脸,又看了看身旁含笑的夏三爷,心里那二十天的焦虑与不安,忽然都化作了踏实的暖意。 天边的晚霞正浓,仿佛在为这对即将并肩前行的兄弟,铺展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德昇的会计办公室,设在大队部的耳房。一张掉漆的木桌,一把三条腿的板凳,还有一个缺了角的算盘。 他对着那串油光发亮的算珠发愁,手指在上面笨拙地拨弄,算错一次就用袖口擦去账本上的墨迹,半天下来,袖口黑得像抹了墨。 “这珠子得用巧劲。”夏三爷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碗苞米糊糊,“当年你爷爷教我算账,说算盘珠子响,日子才能亮。” 他放下碗,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算盘上演示“二一添作五”,算珠碰撞的脆响在小屋里回荡。 德昇跟着学,手指磨出了红痕,夜里躺在床上,指尖还在被子上比划着。 半个月后,他的账本开始变得清晰工整,每一笔工分、每一斤粮食都记得明明白白,连德麟看了都忍不住点头:“不愧是念过大书的,这字比砖窑的线还直。” 1962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盘山农场的电线杆上贴出了征兵告示,红纸黑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 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已经传到了大队里,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报前线的消息。 德麟在大队部的耳房找到了德昇,他刚核完秋收的粮食账,手指上还沾着墨汁。 “德昇,县武装部在招兵。”德麟的声音很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去吧,当兵是光荣的。” 德昇愣住了,手里的算盘珠子啪嗒掉在地上:“可大队的账目......” “有我盯着呢!”德麟打断他,目光望向村口的方向,那里的老槐树上挂着高音喇叭,正播放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不会让咱大队落后,更不会让村里的老老少少饿肚子。爹说得对,男子汉就得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来的家” 德昇看着兄长眼角的细纹,那是常年操劳留下的印记。他想起小时候爹教他们写“国”字,说方框里的“玉”是珍宝,外面的框是城墙,守不住城墙,就护不住珍宝。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算珠在掌心硌出浅浅的红痕。 离家那天,飘着细雪。来接新兵的大解放汽车停在生产队队部的门口。 夏张氏把一篮煮熟的鸡蛋塞进德昇的帆布包。鸡蛋用粗布裹着,还带着余温。 她的手指在德昇军装的第二颗纽扣上停了又停,那是心脏的位置,仿佛想把所有的牵挂都通过这轻轻的触碰传递给儿子。 “到了部队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她的声音有些发颤,眼角的泪痣被泪水浸得发亮。 德麟站在一旁,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拍了拍德昇的肩膀。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带着砖窑的温度,德昇知道,这一拍里有嘱托,有期盼,还有沉甸甸的兄弟情。 列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时光在耳边流淌。 德昇隔着车窗望去,母亲转身离开的背影有些佝偻,风中飘起的白发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系着车站,一头系着他的心,越拉越紧,最终刺痛了眼眶。 列车穿过山海关时,德昇靠在车窗上打盹。城堞的影子在玻璃上掠过,像一道道凝固的历史刻痕。他睁开眼,看见玻璃上的倒影,左边是母亲眼角的泪痣,右边是邻座新兵挺得笔直的脊梁。 破晓的天光从车窗涌入,将这两样东西熔成了一枚发烫的星星,在他的瞳孔里闪闪发亮。 那是家与国的交融,是牵挂与信念的重叠。德昇摸了摸军装口袋里的家书,兄长的字迹在颠簸中仿佛活了过来,砖窑的火光、大队部的算盘、母亲的白发、三爷的书.....所有的画面都在眼前流转,最终凝成一个坚定的信念。 他挺直脊梁,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 远方的天际线正泛起鱼肚白,像极了北大窑砖厂初升的朝阳,带着无尽的希望,照亮了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