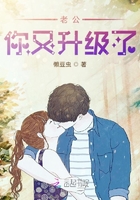小咪的衣食父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雪依然在下,张义芝终于熬不住,半夜披衣坐起,摸黑摸到炕梢的月英,声音像被车轮碾过: “月英,妈给你再缝一床吧。” 月英没应声,只把身子往墙里缩了缩,留给母亲一个冰凉的脊背。 张义芝叹口气,摸出针线包,火柴“嚓”地一亮,照着那双早已变形的手指。线头蘸唾沫,捻了又捻,就是穿不进针眼。第三回,线头分叉,像嘲笑她老了。 老太太忽然把针和线一把攥进掌心,刺破了皮,血珠冒出来,在雪夜灯下像极小的红豆。 月英终于翻过身,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妈,别缝了,再缝多少床,我也暖不过来。” 张义芝没抬头,只把血擦干净,继续穿针。这回穿进了,她扯过枕边一块旧布。那是俊英做棉袄剩下的,蓝底碎白花,在灯影里像结了一层霜。 针落下,第一针扎在布上,也扎在母女之间那层看不见的肉里。 “你嫌我缝得不好”张义芝声音发颤,“当年给你缝鸳鸯,你说一辈子;如今给俊英缝牡丹,你说暖不热。针脚还是这双手,线还是这团棉,怎么就成了错” 月英猛地坐起,头发散乱,像黑夜里炸开的一团火:“错的是花!鸳鸯死了,牡丹活着,我活着,可活得像贼,像影子,像火车一过就被震碎的窗纸!” 她一把扯过炕头那床旧的棉被,用力太猛,一朵花瓣被撕离,红线“嗤”地抽出一截,像伤口里拖出的筋。 张义芝去抢,月英却死死抱住,把脸埋进那团艳红,哭不出声,只剩肩膀一耸一耸,像被风雪折断的芦苇。 张义芝忽然松了手,抬手“啪”地关掉煤油灯。屋里黑得能听见雪片落在屋顶的沙沙声。 老太太摸黑躺下,和闺女并肩,像两具被雪埋住的尸体。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又来了,汽笛劈开夜空。雪光映窗,照出炕上那床被,露出里面雪白的棉絮,像一截骨头。 月英在轰鸣中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铁轨吞没:“妈,我想把鸳鸯被重新缝起来。” 张义芝没睁眼,只伸手摸到闺女冰凉的手指,扣进自己的掌心里:“明儿个天一亮,就去旧箱子里找,拆了的线还在,飞不走的。” 雪声覆盖,火车声远去。黑暗里,母女俩的手指在一处,像两根终于捻成一线的断头棉,谁也说不清是谁在牵着谁。 天快亮时,风停了。月英听见母亲极轻极轻地哼起旧年小调,“狼来了,虎来啦,和尚背着鼓来了……” 那是小时候母亲哄她睡觉时,唱的摇篮曲。调子断断续续,却把一个雪夜缝得密不透风。 月英要再嫁了,张义芝的心又活泛起来了。可是,有了吴玉华的事,没人敢给月英提亲。 年底,小军放假回来了。坐在回城的汽车上,眼前闪过曾经的街景,忽然那么陌生。 小军在脑海里不断的对比,思绪涌上来,不由自主的涌向离开家,去大荒沟插队的那天。 那天,绿色的大解放在盐碱地上哐当哐当跑了小半天,都是一望无际的荒野。 十四岁的小军把脸贴在冰凉的柳条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外套下摆内里的凸起。 那是俊英连夜赶着用月英的人民服改的,针脚密得能挡风,下摆的内里绣了小军的名字。 俊英把小军所有的行李,都写上了小军的名字。能绣上的就绣,绣不了的就刻,刻不了的就贴。总之小军的柳条包里的东西都有名有姓,叫刘军。 “大荒沟快到了!要同学们准备好下车’带好自己的行李!”带队的吆喝声裹着寒气飘起来。 小军赶紧攥紧帆布包,里面除了两件换洗衣裳、三双布鞋、语文课本和一本《青春之歌》,还有张义芝塞的一小包红糖,用油纸包了三层,说是让她给照顾自己的老乡送个礼。 脚刚沾到大荒沟的土地,小军就打了个寒颤。 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远处的林子光秃秃的,枝桠像瘦骨嶙峋的手抓着铅灰色的天,只有几间土坯房蹲在荒地里,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没等飘高,就被北风扯成了碎絮。 “欢迎同学们!”一个裹着蓝头巾的妇女,笑着迎上来,手里端着个破了口的搪瓷缸,热气裹着玉米糊糊的香飘过来。 她是大队书记家的媳妇刘春玲,嗓门亮得像挂在屋檐下的冰棱:“快跟俺走,炕都烧暖了,别冻着咱城里来的闺女。” 大家跟着刘春玲往村里走,灰土一踩上去,腾起一层灰雾,没到脚踝。 小军是汗脚穿的是小季穿不下的解放鞋,捂了这么长时间,鞋壳子里面很快就湿了,一走一打滑。 刘春玲看出来了,故意放慢了脚步,和她搭话,“同学贵姓啊” “刘军,”小军没出过远门,羞怯怯的答话。 “太巧了,我也姓刘,咱是一家子!”刘春玲大嗓门,爽快的笑了起来。 小军也跟着笑了起来,可是那脸色比哭还难看。 到了刘春玲家,土炕占了半间屋,炕桌上摆着一碟咸菜、两个贴饼子。 刘春玲把搪瓷缸递过来:“快喝口热的,路上肯定没吃好。” “是滴水未尽,啥也没吃好吗”小军心里说,早就饿的潜心贴后背了。她捧着缸子,玉米糊糊的热气熏得眼睛发潮。 这是她离开家后,喝到的第一口热乎东西。 “大妹子,咱这还没有青年点,你就暂时住我家里,我家没别人,你姐夫是咱大荒大队的书记。”刘春玲说着,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小军点点头,有些茫茫然,“都行,挺好的。”她本就是个没主意的人,从小到大都在母亲身边,上面的哥哥姐姐哪有什么事能轮到她做主 第二天鸡叫头遍,小军就被刘春玲叫了起来。 她揉着发红的眼睛穿好衣服,刚掀开门帘就愣了:院子里的水缸满满的,屋檐下的蒿草能有半尺长,风刮得院门上的破布帘哗哗响。 “今天跟俺去拾粪,咱生产队里的地要施肥,这活儿虽糙,却是正经的农活,也是最轻巧的活儿了。”刘春玲趴在她耳边小声说,递给她一副小粪筐,还有个磨得发亮的粪叉。 小军跟着一群婶子大娘往大地里走,解放鞋的鞋底踩在硬怆怆的盐碱地,脚下咯吱响。 她学着大家的样子,看见粪就用粪叉叉进筐里。管它牛粪马粪还是驴粪,反是她也分不清楚。可没一会儿,她的手就酸得不听使唤。粪叉好几次滑落在地上,裤脚和袖子也沾了泥。 刘春玲看见了,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她:“俺这手套旧是旧,好用,你戴着。” 那手套里还带着刘春玲的体温,小军攥着它,突然就不觉得风那么冷了。 拾粪的活儿一干就是三个月。冬天已悄悄降临,大荒沟淹没在茫茫的白雪之中。 小军的手背还是冻出了冻疮,红肿的皮肤上裂着小口子,一沾热水就钻心地疼。 刘春玲看在眼里,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就把小军拉到油灯下,从柜子里翻出个小瓷瓶,倒出些黄澄澄的猪油:“这是俺攒的,抹在冻疮上,比啥药膏都管用。” 油灯的光昏黄柔和,映着刘春玲眼角的细纹,小军突然想起妈妈给她涂护手霜的样子,眼泪差点掉下来。 没过多久,队里开始刨冻粪。盐碱地冻得像铁块,一镐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子,震得胳膊发麻。 小军跟在刘春玲身边,学着她的样子把镐头抡圆了往下砸,没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碰到冻得通红的耳朵就凉得刺骨。 “歇会儿吧,别硬撑。”刘春玲递过来一块烤红薯,“你这年纪,在城里还在学校念课文呢,到这儿来遭这份罪,委屈你了。” 小军咬了口红薯,甜丝丝的热气顺着喉咙往下滑,她摇了摇头:“不委屈,俺也能为生产队里干活了。” 日子一天天过,小军渐渐适应了大荒沟的生活。 她学会了用井里的凉水洗脸,学会了把贴饼子烤得外焦里嫩,还学会了听着鸡叫判断时辰。 只是每到晚上,她还是会拿出语文课本,就着油灯的光看上几页。 刘春玲家的小女儿丫蛋才八岁,总爱凑到她身边,缠着她讲书里的故事。 “林道静真勇敢,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丫蛋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小军姐,你穿红棉袄的样子,也像书里的英雄。” 小军摸了摸她的头,心里忽然觉得,自己带来的不只是一本书,还有一份从城里的课桌边带来的念想。 腊月里下了场大雪,没过了膝盖。队里的牛棚被雪压塌了一角。 男人们要修牛棚。刘春玲带着队里的女人去圈牛,小军也跟着去了。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和丫蛋一起抱着稻草往牛棚里送,稻草上的雪化了,把棉袄的下摆浸湿,冻得硬邦邦的。 牛棚修到一半,刘春玲突然喊了一声:“不好,牛要跑!” 只见拴在角落里的老黄牛挣断了缰绳,朝着门口冲过去。 那是队里最能干活的牛,开春耕地全靠它。 刘春玲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伸手去抓缰绳。可老黄牛受了惊,力气大得很,一下子就把她带倒在雪地里,棉袄沾满了雪,像朵被雪压弯的花。 就在这时,小军扑了过来,一把抓住缰绳,使劲往回拽,老黄牛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 小军从雪地里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 刘春玲赶紧把她拉到牛棚里,用干草擦着她身上的雪:“你这孩子,不要命了牛惊了多危险!” 小军看着刘春玲冻得发紫的脸,小声说:“俺怕牛跑丢了,队里开春还得用它耕地呢。” 刘春玲愣了一下,随即拍了拍她的肩膀:“好闺女,真是个懂事的。” 那天晚上,刘春玲特意煮了个鸡蛋,剥了壳递到小军手里:“快吃,补补身子,今天可吓坏俺了。” 鸡蛋的香味飘在屋里,小军吃着鸡蛋,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在大荒沟,她又有了一个家。 年后开春,盐碱地慢慢解冻,队里开始忙着春耕。 小军跟着春杏学撒种,手里攥着金黄的种子,往翻好的土里撒。 风里带着泥土的腥气,阳光晒在身上,暖烘烘的。一天下来,她的腰都直不起来,可看着土里的种子,她心里却格外踏实。 这些种子,春天发芽,秋天就能结出粮食,就像她在大荒沟的日子,慢慢长出了希望。 有一天,她在地里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小麻雀,羽毛湿漉漉的,翅膀还流着血。 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回家,用刘春玲给的布条包扎好伤口,每天省下半个贴饼子掰碎了喂它。 小麻雀渐渐好了起来,每天都在屋檐下蹦蹦跳跳,丫蛋也总爱过来跟它玩,院子里多了不少笑声。 夏天的时候,大荒沟的杨树林变得郁郁葱葱,地里的玉米长得比小军还高。 她和丫蛋一起去河边摸鱼,去原野里挖野菜,红棉袄被风吹得飘起来,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小军收到了的信,是张义芝写来的,说家里一切都好,让她在这边照顾好自己,还说等秋天了,想寄件新毛衣过来。 小军拿着信,蹲在院子里看了好几遍,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了字迹。 刘春玲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想家里了吧等年根儿底下了,俺跟书记说说,让你回家看看。” 小军抬起头,看着刘春玲,用力点了点头。 这年秋收的时候,大荒沟的收成格外的好。盐碱地上满是金黄的玉米和沉甸甸的高粱。 小军跟着队里的人一起收割,身上沾了不少玉米叶的绿,可她一点也不在意。她学着婶子们的样子掰玉米,手指被玉米叶划了小口子,也只是随便擦了擦,继续干活。 看着装满粮食的马车从地里往队里拉,她心里格外高兴。这地里的粮食,有她撒的种子,有她流的汗。 收割完的那天晚上,队里办了庆丰收的晚会。大家围着篝火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声音亮得能传出好远。 小军也跟着大家一起唱,脸上的笑容在火光里格外鲜艳。 她看着身边笑着的刘春玲、闹着的丫蛋,看着远处黑沉沉的土地,突然觉得,十四岁的这一年,她在大荒沟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里学的还要多。 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吃苦,还学会了爱。爱这片黑土地,爱这里的人。 那天晚上,小军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手里攥着妈妈寄来的信。 她想起刚到大荒沟的时候,自己还哭着想家,可现在,她觉得这里也是她的家了。 第二天早上,小军早早地起了床,跟着刘春玲去地里拾玉米茬。 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黑土地上,洒在她的身上,暖洋洋的。 她弯着腰拾玉米茬,脚步比以前更稳了。风里带着秋天的凉意,可她一点也不觉得冷。 她知道,她的十四岁,在大荒沟的土地上,热烈又明亮,永远都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