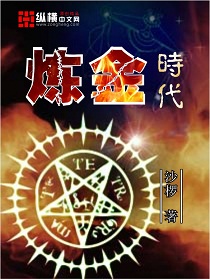琼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雨还在下。 我和魔尊站在公交站台的铁皮棚下,头顶是那把黑伞,伞面上银纹幽幽,像活物般在雨水的浸润中微微闪烁。 我抱着纸箱,箱角已被雨水泡软,边缘开始发毛。 冷风一吹,湿透的外套贴在背上,寒意刺骨。 忽然,一股香气飘来。 不是雨水的土腥,也不是街边小吃摊的油烟,而是一缕极淡的檀香,混着某种陈旧经卷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钻进鼻腔。 我心头一跳。 这香味……我在奶奶的老宅里闻过。 每逢初一十五,她都会在堂屋点一炉香,说是“净尘辟邪”。 可这雨夜里,哪来的檀香 我下意识低头,却见伞骨上那些银纹,竟在雨水的冲刷下缓缓流动!它们像细小的银蛇,顺着水流的方向,沿着伞柄,一寸寸爬上我的手腕,渗入皮肤。 “别动。”魔尊突然低喝。 他一把将我拽向站台角落,动作迅猛得让我踉跄跌倒。 就在我原地站定的下一秒—— “轰!” 一辆公交车疾驰而过,溅起半米高的水墙。 车头灯刺眼,映出车身上一张巨大的海报: 寻人启事:林默言,女,23岁,精神异常,走失于清虚观附近……” 照片是我的,是公司年会时拍的,笑容灿烂,却被配上“精神病人”四个黑字,像一道判决。 我浑身发冷。 柳玄舟……他已经把我定义为“疯子”了。 一旦我再提及异界、玉佩、魔尊,没人会信我,只会说我病情加重。 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满脸戾气:“找死啊!不长眼!”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红色护身符,绣着八卦图案。 魔尊冷冷盯着那符。 突然—— “啪!” 护身符毫无征兆地炸裂!布片四散,露出里面一张黄纸符咒,瞬间被雨水打湿,墨迹晕开,显出扭曲的符文。 下一秒,整张符“嗤”地燃烧,化作黑灰,随风飘散。 司机愣住,摸着脖子喃喃:“妈的……又坏了这都第三个了……” 我认出了那符。 和玄渊拍卖行里卖的“平安符”一模一样——我曾在官网上见过,售价999元,号称“开光镇邪”。 可那根本不是护身符,而是控魂咒的载体。 魔尊冷笑:“用这种劣质咒术操控凡人,让他骂你、驱赶你、把你当成疯子……柳玄舟倒是越来越没格调了。三百年前,他好歹还懂点规矩。” 我咬紧牙关,盯着那辆远去的公交车。 它开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 司机的影子在车窗上扭曲,黑线缠绕,比网吧里更密。 他已经被完全控制了。 “他想让我无处可去。”我低声说,“让整个城市都视我为异类。” “成功了一半。”魔尊语气平静,“但你忘了,疯子……往往才是看见真相的人。” 我苦笑。 末班车开走了,站台陷入短暂的死寂。 雨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哗啦啦地敲打着铁皮棚顶。 就在这时,站台对面的电子广告牌突然“滋”地一闪,屏幕上的奶茶广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航拍视频。 画面抖动,像是用手机拍的。 镜头从高空缓缓推进,穿过雨幕,落在城郊那片荒山之上——清虚观。 我的心跳骤停。 镜头拉近,破败的殿宇、倒塌的围墙、那口悬在石架上的铜钟……一切如昨夜。 可就在我以为这只是段普通影像时,画面突然定格。 镜头聚焦在三清殿的屋脊上。 那里,坐着一个人。 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挽起,背影清瘦,肩线笔直。 她静静地望着远方,一动不动,仿佛已坐了百年。 我的呼吸停滞了。 那背影……那衣着……那挽发的姿态…… 是奶奶。 年轻时的奶奶。 我曾在她旧相册里见过这张照片——那是她二十岁时,在道观修行的日子。 可她已经死了三年了。 “这……这是什么”我声音发抖,指甲掐进纸箱边缘。 魔尊盯着屏幕,眼神凝重:“幻影回溯。柳玄舟在用‘记忆之咒’,重现她生前的影像。” “为什么” “不是他。”魔尊摇头,“是道观。那地方浸透了你奶奶的灵力,她的执念太深,哪怕死了,影子也留在那里。柳玄舟只是……借用了它。” 屏幕上的“奶奶”忽然微微侧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虽然看不到脸,但我仿佛能感觉到——她在看我。 在看这个站在雨夜里、抱着纸箱、被全世界驱逐的孙女。 一股热流猛地冲上眼眶。 我想喊她,想冲进屏幕,想扑进她怀里大哭一场,告诉她我好怕,我好累,我想回家…… 可我知道,那只是影子。 是记忆的残渣,是灵力的回响。 不是她。 广告牌的屏幕突然闪烁几下,画面开始扭曲。 那屋脊上的身影缓缓抬起手,指向某个方向—— 不是我,也不是道观。 而是城南。 镜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拉远,穿过山林、河流、城市,最终定格在一片被铁栏围住的老宅区——河道转弯处,几栋民国风的青砖小楼静静矗立,门口挂着一块鎏金招牌: “玄渊别院 私人会所” 水月庵旧址。 第二块玉佩的线索,就藏在那里。 广告牌“啪”地黑屏,恢复成奶茶广告。 雨声重新填满耳朵。 我站在原地,浑身湿透,心却烧了起来。 柳玄舟用寻人启事污我名声,用公交司机驱我于路,又用奶奶的幻影引我入局。 他步步为营,就是要我主动踏入他的巢穴。 可他忘了。 奶奶留给我的,不只是恐惧和逃亡。 还有火种。 我低头看向手腕——伞骨上的银纹已退去,但皮肤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银色痕迹,像一道隐形的符。 魔尊收起伞,黑袍在雨中猎猎作响。 “你还要去”他问。 “当然。”我抹去脸上的雨水,将纸箱抱得更紧,“他以为把我逼到绝路,我就会求他。” 我抬头,望向城南的方向。 “可他不知道——绝路的尽头,才是我奶奶真正留给我的东西。” 雨还在下。 但我的玉佩,正贴着胸口,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