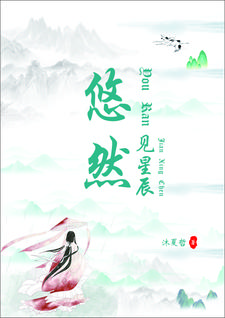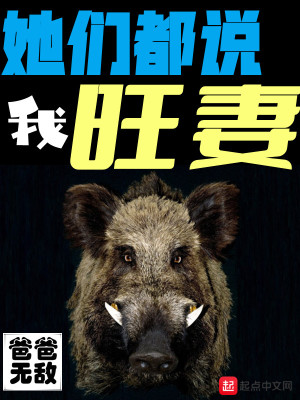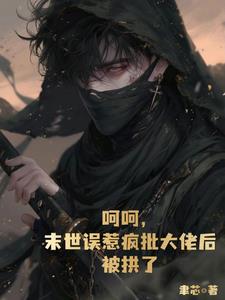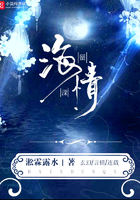水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授以高爵厚禄,委以家国重任,兵临而弃城,陷百姓于水火,真犬马之不如也!”
陆太后气极而笑,当即摔坏了一套茶盏。
端平帝和内侍在一旁见此情形,皆被吓得惶惶然不敢言语。最终还是沈昭起身请示。“娘娘,当务之急是请诸公入殿,商议应对之策。”
陆太后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怒火,“知会诸位阁臣,六部堂官,五军都督,一柱香后,于御书房议事。”
沈昭见此,便向陆太后告退。
哪知陆太后却制止了她。
“你同我一起,于珠帘后听事罢。”
“这……”
沈昭瞪大了眼睛,全然不知所措。
一旁的内侍亦是惊诧不已,就连小小的端平帝都好奇地向陆太后看去,因为他也知道这不合礼法。
“西北之事,你比我要清楚。”
沈昭愣了一下。
陆太后这是担心朝臣欺他们孤儿寡母不知事,最终以权谋私,反倒将国事置于一侧。纵使此事为无上恩宠,沈昭却不免要提醒一句。
“朝中韩阁老,谢大人等皆是肱骨之臣,娘娘大可倚仗。”
陆太后深深看了她一眼,并不言语。沈昭见此,不禁默然。陆太后以为朝臣皆有私心,遂不尽意,可又怎会以为她没有私心呢或者陆太后是觉得她眼下过于势微,纵使有私心,也不得不依附于她。
……
御书房内,朝中重臣皆侯于此。
沈昭低垂着头,跟在陆太后身后从侧门而入,如随侍的宫女一般。
端平帝坐在龙案前,在其右侧的偏堂则挂上了珠帘,陆太后便坐在后头,同朝臣言事。
“西北军情,诸公已然知晓,不知可有应对之策”
“早在永明九年,穆宗皇帝便下令重开宁夏榆林等处马市,与鞑靼互通物什。然其行事毫不避讳,可见已不将我朝威严放在眼中。”
已调回京师任前军都督的诚意侯不偏不倚地回话。
虽则言语隐晦,可众人皆知重开马市即为大周与鞑靼议和。然距今不过五六年,对方却公然进犯,足见已未将国朝放在眼里。
陆太后知道他有同鞑靼作战的经验,当下便问道:“那依严都督之见,此事该如何应对”
“当务之急是守住雁门关,从京师大营调兵前去救助,而大同等地则从宣府,紫荆关调兵。唯有这两处地方守住,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
诚意侯地回话依旧中规中矩。
不过此事略显古怪,毕竟攻城非一朝一夕之事,且凛冬之际行军并非易事。虽则京师变故让朝廷无暇顾及西北,可鞑靼绝无可能在短短月余便攻陷数城。
沈昭思及此处,复又想起了西北传来的塘报。可她之前匆匆一瞥,并未瞧出不妥来,便又在陆太后耳侧低语道:“娘娘,西北塘报怕是有异。凛冬之际,鞑靼行事不可能如此迅猛。”
听完这话,陆太后不禁怔了一下。
她对军事并不了解,可深冬雪重,不宜行军她还是知道的。可为何她之前将塘报传给众臣,无人提出疑虑反倒是沈昭言及此事。
她的脸色不由得沉了些许。
“对于这份塘报,诸公可有异议”
“臣有异议。”
说话的是兵部尚书管考易,他曾奉命戍边,对于西北之事比寻常文臣更加了解。
“深冬雪重,西北风沙又大,行军殊为不易。鞑靼不可能在短短一月之内,攻破数镇。西北军情迟迟不入京师,恐是有人趁新帝践祚,事务更替之际拦截此事。”
这话一出,当下众人神色各异。
鞑靼本事再通天,也不至于将他们的塘报拦截。也就是说唯有本朝人……其用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沈昭想到自己的猜测成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在京师这繁华地争权夺利,享尽温柔富贵,何尝想到千里之外的百姓正遭受异贼的侵犯。可笑的是,他们竟还想着端拱为政,太平兴国。
“此事须当彻查。”
首辅窦敬言不紧不慢地发话。
不待陆太后有所回复,永嘉侯便沉声说道:“我记得严都督曾任宁夏总兵,与鞑靼交战数年,对于他们作战布局莫非不清楚么竟不知这份塘报的诡异之处。”
诚意侯当即反唇相讥。
“云都督任辽东总兵近十年,亦是戍边之将,战场风云变幻怎不见你瞧出来你说我未有先见之明,我到觉得你隐而不言,其心可诛。”
“严都督此言未免强词夺理!”
永嘉侯冷笑一声。
“朝野皆知你当初是穆宗皇帝钦点的戍边大将,在与鞑靼对战之时屡建战功,如今却连一份塘报的真假都瞧不出。若非你刻意欺瞒,那往日功勋便为虚假。”
“云都督可要谨言慎语!”
诚意侯阴沉着脸,嘲讽道。
“管大人只说塘报恐是旁人拦截,并无实据。你如此表态,是蓄意构陷,还是急于摆脱嫌疑”
“严都督——”
“好了!”
永嘉侯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陆太后开口打断。
“御书房内,商议朝事,你们却如市井妇人一般相互指责,成何体统!有这份精力,不如想想如何解决此事!”
“臣愿请命,领兵逐寇!”
永嘉侯当即回话。
陆太后还未表态,诚意侯便紧跟着道:“禀娘娘,微臣愿尽绵薄之力,领兵出征。”
这两人今日倒像杠上了一般,可他们往日里并无仇怨。陆太后见他们两人誓要打上一场的模样,不禁犹疑起来。沈昭见此,便又在她耳侧低语。
片刻后,陆太后说道:“韩阁老,你今日一直寡言,可是对此有异议”
韩廷贤原是准备打太极的,见陆太后的目光转到了自己身上,才不得不回话,“非是有异议,微臣只是在考量如何应对。”
见陆太后应了一声,便又说道:“正如两位都督所言,该派兵遣将,前去援助。”
“阁老以为谁更合适”
“这……”韩廷贤见她追问,顿了一下,“两人皆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各有所长,无论谁去都只会旗开得胜。”
又是个明哲保身的。
陆太后脸色沉了一下。
沈昭也略感诧异。
她让陆太后询问韩廷贤,本是笃定对方有解决之法,不想竟是这般态度。实在不像他素日为人。莫非是深觉这是一趟浑水,所以不愿趟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何不趁机行事以得权柄
而永嘉侯和诚意侯这两人……究竟谁才是用心险恶者,却不明了。
自新帝践祚以来,这是陆太后第一次听政处事,却遇到了这样的阻扰。朝臣们根本未将她放在眼里,即便是极力支持慕容祰继位的韩廷贤等人。
“我听闻先帝在世时,多是倚仗诸公,始有太康,永明盛世。而今西北失事,百姓困于水火。国难当前,诸公不念君恩,沉于集权便也罢了。又怎可在国事之上推三阻四,避而不言。
如此行事,可当得上我大周朝的肱骨之臣,又如何对得起先帝嘱托,对得住圣贤之言!陛下年幼,尚不知事,而我一介女流,不通朝政,恐负先帝之托,唯望诸公尽绵薄之力,护住大周江山。”
陆太后字字泣血,句句诛心。
朝臣们面面相觑,不禁赧然。
“臣等必将竭尽全力,不负先帝所托。”
陆太后暗暗颔首,又道:“既如此,诸公对西北之事可有良策,若点兵遣将,又该命何人前往”
“臣以为,当设戍边大将,总督三镇,随时调派各镇军士,以应事变。往年江浙两广之地,时有倭寇之乱,京中调派不及,多设总督,掌数省之军政,以防事乱。”
说话的是刚升工部尚书并入为东阁大学士的廖思浦。虽未给出明确答复,其意却不言而喻。想必这三镇总督的人选他也早已有数。只是历来封疆大吏虽不少,可总督西北军政的却从未有过。此举无外乎是欲掌西北军权。
即使陆太后再不懂朝事,也对此事颇为存疑。“总督西北之事,从未有之,如此恐是不合情理。”
“娘娘此言差矣。”
程党事败后,朝野势力经过一番血洗,内阁九卿皆有变动。如新任的刑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郭振便是由南京吏部尚书转任。
“此次西北事败,多是因各方并无联络,不通情势,兵力调配不及,给了异贼可乘之机,以致城池失守。若可总督军务,整合兵力,边疆必定固若金汤。”
“这……”
陆太后一时语塞。
她当然知晓这是对方欲掌权而说出的理由,可若反驳,恐是垂帘听政亦无一席之地。只是这郭振分明由谢时镇举荐入京,怎会与窦党同进退
“娘娘不通军务,故有所疑虑,不如请示诸公,以做定夺。”
郭振行了一礼。
此言一出,陆太后神色骤变。郭振此举,分明未将她放在眼里。恐其深觉女主乱政,对朝廷颇为不满。
“郭大人此言差矣。自达延汗继位后,鞑靼兵力日渐强盛,右翼济农巴尔斯博罗特野心勃勃,屡次犯边。此次山西大同皆受其扰,而榆林兵力稀少。鞑靼又主攻此处,山西大同虽调兵援助,终落下风。故当务之急非是设戍边大将,而是操练军士,增强兵力。”
窦党意在西北兵权,沈昭若未听事,自无力阻扰。然既旁听政事,便不会置之不理。
不得不说,朝野内外少有如她这般了解西北军情者。
当下一片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