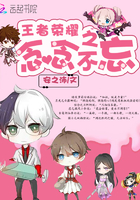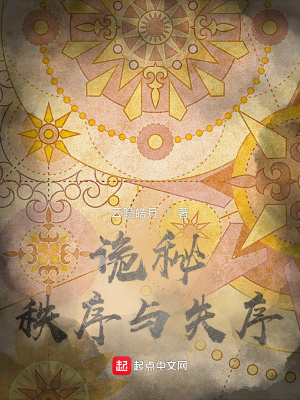月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清早的雾从护城河上退去。 许都像刚出炉的器物,温热尚存,外壁却还带着夜里落下的清凉。 太学南墙的三盏“问字灯”先于鸡鸣亮了,灯焰稳,像按住城心的三根指。焦尾古琴覆着薄绢,缺弦处透出干净的木香。 郭嘉在廊下立了一会,指腹轻触栏杆上的水迹,水凉,心却在热——第三日账将尽,反扑既起亦伏,鼎火稳住。他本该去东廊看账,却被门外一声轻轻的车辘响牵住了耳。 驿馆的小车停在门外。 车身旧,车笼却绑得极紧,一层油布,外罩柘木箱,箱面钉着细铁,铁痕不华,钉位却像按着一种看不见的律。 卫峥领着两名驿卒进门,将木箱抬到廊下。木箱不大,沉得很。箱角印着一个极细的戳记,像月牙,又像一弯钩。戳记下只有两字:月英。 郭嘉挑了挑眉:“荆州” 卫峥拱手:“南路商脉送来。送箱之人只言‘黄门老生致祭酒’,不留姓名,只留了一封缃色书。” 荀彧闻声自内出来,笑意清浅:“黄门老生,恐是黄承彦。” “黄承彦”程昱顺手把门阖上一半,“襄阳黄公,怪癖人,喜女婿多语。” “他语不多,笑多。”郭嘉抬手,“开。” 铁钉先以细锥松一丝,再以榔头按着次序敲出,连声都不乱。箱盖起处,冷香扑面。不是香料,是木的气。 箱内第一层是一架拆作三截的木梁,梁上刻着密匝匝的刻度,刻度之间以铜线连缀,线头扣成小小的环。第二层是一张图,绢上墨迹如丝,细到几乎惹人厌烦。 第三层,一只静止的木雀,羽薄,喙锐,腹部用细丝缝合着一个风袋。再底下,是一封缃色书,封口压的印,正是那弯细细的“月”。 荀攸将木雀举起,轻吹一口气,雀的翅先抖了一下,随后居然在廊下绕了一小圈,落回他掌心。众人皆笑。笑声未散,卫峥把那张绢图平铺在案——只是看了一眼,荀彧就忍不住按住了它的角。 “好大一口气。”他低声,“像是把城的风也拿来画了。” 绢上不是山川,不是城廓,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弧,弧上有细不可见的点。 弧之间以极细的线相引,线头缀着小字:比方、阅风、衡声、问灯、暗秤、倒锁。字旁有短注,不言其形,只言其意:风从何处来,便从何处去;人从何处聚,便从何处散;灯不为照,为问;锁不为闭,为慢。 “这是谁的手”曹操在后问,语气并不锋,倒像在看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笑话,“荆州出工巧之士,此图却非匠人的气,倒像一位看书的。” “黄公有女,传闻巧而不饰。名曰月英。”荀彧笑得浅,“有传言说其貌不扬,黄公笑曰——‘我女贤才,何必貌’。” 郭嘉拆了缃书,先不读字,先闻书上的气。书不香,却干;不香,才真。第一行字用小字横开:“许都为鼎,鼎腹之气,不可尽凭门钥与仓粟。为君画《阅风图》一纸,愿以风为引,以愿为衡,以灯为谱。” 他停了一下,唇角弯起,把字读给众人听。 “以风为引,以愿为衡,以灯为谱。”荀攸重复,眼里亮了,“她是要将我们‘问字灯’与‘鬼斧’对风。” “风是什么”典韦挠挠后颈,“我看得见灯,看不见风。” “风在人的脚下。”郭嘉笑,“脚步出声,礼便知;脚步无声,‘沟’便知。她这张‘阅风图’,是把我们的‘听雨沟’往前推了一步——风未起,人已动,灯未问,心先紧。” 曹操用指节叩了一下案角:“她如何知‘听雨沟’” “荆州商路日日进出。市署的‘回声井’吃了几口风,风便会带走笑话。笑话走远,就成了消息。” 郭嘉把缃书翻到第二页,纸背忽浮出一个小小的纹章:一轮新月,月下是一枚匠印,“黄”。 他读到后面几行,轻声:“‘九府工图’之法善,用以活人;‘鬼斧’之谋巧,用以止人;两者合,城得呼吸。然鼎既成阵,犹欠一‘衡’:衡风之器,不在器,在人。愿借一案:八风问灯。灯问人,人应风,风折为律,律再归灯。” “八风问灯”荀彧笑,“八方来风,各设一灯” “差不多。她画了一个很小的台。”郭嘉指着图,“台中央一盏‘愿灯’,八方各置一盏‘问灯’,灯芯不同,长短不同。风过,其色先动;人至,其影先变。灯不言,灯影会说话。” “灯影如何说”许褚眯起眼。 “灯影伸得急,脚步就会快;影缩得短,人心就会紧;影左右撇,人便犹豫;影稳,心稳。”郭嘉把那截铜线捻在指尖,“此图还有一物:细线为‘衡’,线上扣环为‘数’——那木梁刻度,便是‘风梁’。按她的说法,‘风梁’架在‘听雨沟’上,沟收声,梁记影,再用‘暗仓秤’的式样做一只‘灯秤’,灯影一落,秤枝自重,重量不记名,只记风。” “听起来像戏法。”程昱喃喃。 “戏法从来是给人看的。”郭嘉微笑,“这回我们是要让‘风’看人。” 他把缃书合上,手指轻轻在封口处按了一下,按得很稳。胸口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正好松了一线。他抬眼,目光落在众人身上:“此女在荆州,不可召。不召,则如何用” “南工北用。”卫峥答得利落,“以商路为筋,以驿站为骨,以‘影子钱庄’为血,东西往返,图与件皆不入官府账册,只入‘愿’。” “礼上不挂名,账上不写姓。”荀攸笑,“她只在图上落一个‘月’字,便够。” “还有一件。”荀彧斟酌,“荆州在刘表之下。黄公是名士,蔡氏在侧。若此女之才为人窥见,恐有阻隔。” “所以不显。”郭嘉把木雀拿起,吹一口气,木雀再绕廊一周,“显在事,不显在人。今日若能立‘八风问灯’于太学南墙,明日便以‘问灯’之名行‘阅风’之实。看灯者不觉,写‘愿’者不觉,只有风知。至于荆州——” 他顿了顿,唇边那一点笑更浅,“荆州有女,名曰月英。她知道如何藏。” “你见过她”荀彧忽问。 “未曾。”郭嘉摇头,“见过她的字,便似见过了。字不修饰,笔不轻飘。不会用香。”他说完,像想到什么,低声又添了一句,“她在字里,设了一道‘空’。” “空”程昱挑眉。 “无弦。”郭嘉道,“她劝我,焦尾缺弦可以不接,先让城自己在‘空’上找声。她在书末写了八个字:‘弦在心上,不在琴上。’” 曹操笑出声,笑里有赞:“善言者。” —— 午前,东廊小议散。 将作监丞领匠徒入太学南墙,按图试作一台“八风问灯”。 台不过半人高,中央一盏“愿灯”,周围八盏小灯按八风排布:东为条,西为劲,南为薰,北为清,东北为景,东南为风,西南为奥,西北为凉。 灯芯各半寸有差,灯罩厚薄不同。台下埋一条细细的石槽,槽边架着“风梁”。礼官在灯下站了良久,终拍掌一笑:“人未至,灯先问。问完,再写字,写得服气。” 孩子们好奇,把小手伸到灯旁。灯影轻伸,像在逗笑。 一个少年对着“愿灯”作揖:“小灯小灯,愿在何处”他自己笑:“在你心上。”笑声传开,像把昨夜的残潮也冲淡了些。 “问字灯”旁新添一小牌,写“安在何处”,字下按着天子昨日的印。人群边有几张脸看得久,肩背便慢慢垂下来,手握得不那么紧了。影子退出半寸,又回到灯下。 市署西廊,“回声井”里今天吃到一句古怪的话:“荆州来女,障人心。” 鼓声嗡了一下,像被鱼刺了一刺,随即平。账房先生把竹简上的四字翻过来,写“问”。问什么问谁说的问哪里来的问到第三句,话就没了——三句不过,流言不成。 下午,北门“倒锁”前出现了半面陌生的旗,旗上画一钩月,月下两点小字,远远看像“月英”。 许褚把旗按下来,不折,只叫人送去城中布坊换作白布,白布上写“愿”字一枚,再还给来客。来客接了,愣一愣,笑,折旗,走。 许褚看着他的背影,粗声粗气地低声自语:“灯比刀软,软得过分,却好使。” —— 黄昏,东廊更静。郭嘉独自把“阅风图”铺在案上。胸口那只手又往内抠了一下,他把疼意当作一阵风,风过,指下的图也动了一动。 他在图边空白处添了几笔,把“八风问灯”的台数减了一,改为“七问一空”。 荀彧来时,恰看见这笔:“为何留‘空’” “给城。”郭嘉道,“也给她。” “她”荀彧笑,“你倒像已认识她。” “认识一个字。”郭嘉把缃书最后一行给他看。纸末,八字之后,又添一行小小的注:“若城为琴,弦须三处。一在心,一在风,一在……空。”空字旁有一点极淡的墨,像不小心落下,又像故意留下。 “故意。”荀彧看了很久,“好女子。” “好女子。”郭嘉也笑,笑意未落,门外忽有急足。子烈进门,拱手:“‘回声井’又鸣。有几句不净的话,是冲着‘八风问灯’来的——说‘以灯惑众,以女乱政’。” “井吃了”郭嘉问。 “吃了。”子烈答,“未出三句。” “谁抛的” “市上小店伙计,嗓子尖,背后有人捅。他自己不知。”子烈顿了顿,“要不要动” “不动。”郭嘉把缃书轻轻盖住,“让灯自己回。明日早,‘八风问灯’前请一位老人,一位裁缝,一位农人,一位读书人,让他们各写一个‘愿’字。四个‘愿’,四个字,四样字。写完,叫读书人读两句书,叫裁缝剪一段衣,叫农人在‘暗秤’上过一担米,叫老人坐在灯下歇一歇。歇够了,市上的话就会自己死。” “为什么”子烈不明白。 “因为风看到人。”郭嘉道,“灯看到手。手稳了,嘴就不乱。” 子烈应诺退下。 —— 夜里,太学南墙风小,灯影平。 焦尾覆绢。鸩站在灯后暗角,看灯不看人。她近来手更稳,影更薄,连风也难以托起她的衣角。她忽听见极微的一声“叮”。不是铃,是金属碰木的轻声。 她侧耳,声从“风梁”而来,是扣环滑过刻度的轻摩。她顺声望去,一个身影站在灯外,不向前,不远避。那人背很直,着淡青衣,袖口简净。 她没有遮面,却像把自己藏在了灯影之外,不为灯照,只让灯悄悄落在她的指背。 “可愿写字”礼官上前递了笔。 她摇头,轻声:“我写过。”声音像风里的一点温,既不热,也不冷。礼官怔了怔,退开一步。她折身,只在灯下停了一息,便转身入人群。 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倒也不追。她知道,城里今日多了一个会用“空”的人。她悄悄把袖中的一张小纸塞到“风梁”的刻度旁。纸上写一个字:安。她把字按得很轻,像给梁上盖了一层看不见的软。 —— 子夜前后,丞相府里只留半盏灯。 郭嘉把缃书压在“阅风图”的角上,侧身靠椅。 胸中的“龙煞”像久不咳的风,藏在肺叶边缘,时不时伸出一指,又缩回去。他不去追,只在那根看不见的弦抖的时候,让自己数三息,息短,息长,息平。 “子奉。”曹操的脚步来了又轻,像怕把灯吹灭。他在案前停住,指背轻敲桌沿,看了一眼那只木雀,“这雀,是她送的” “应是。”郭嘉笑,“风袋做得好。她懂‘风’,也懂人。”他顿了顿,“丞相,此女不纳。纳之,荆州必警;不纳,荆州不疑。她在荆州,我们在许都,各在各的‘空’里。空拉开,线才好走。” “我不纳人,只纳术。”曹操也笑,“明日账出,‘八风问灯’立,便再加一条木牌:‘愿在何处——在手上。’手不稳,字写不好,秤挑不齐,灯也会抖。” “再加一条。”郭嘉道,“‘祖在何处——在门外。’在门外,便不进灯里扰。” “好。”曹操点头,忽然指着图上一个小小的圆问,“这处为何空着” “给她。”郭嘉答,“她若有意,便在荆州立一处‘女工之台’,台不写名,台不问礼,只问风。风南来北往,带着‘愿’之影过江,过道,过驿站。我们不用收,只要听。听到某一日,风自己会回来。” 曹操长长地“嗯”了一声:“好个‘风’。” 他抬手把郭嘉肩头按了按,像按在一只将要横冲直撞的兽背上,却不压,只让它知道自己被看见。 “去睡。”他说。 “稍。”郭嘉笑,仍用天子那一字。他合上眼之前,手在案上一摸,把那只木雀挪近了“阅风图”的“空”。木雀不动,却像靠在了一阵软风上。 —— 翌日卯时,太学南墙前立了小小的台——“八风问灯”。 灯未问,人已聚。礼官将四人请至灯下:一位腰驼的老人、一位手巧的裁缝、一位挑担的农人、一位衣袖带墨的读书人。四人各写“愿”。四个字四种笔。 老人的“愿”有点颤,却很直;裁缝的“愿”收针一般利落;农人的“愿”重在底,厚;读书人的“愿”在中锋,干净。 写毕,裁缝剪了一段衣边,剪口齐,灯影也齐;农人挑过“暗秤”,秤臂不喊,红漆露得适寸;读书人朗朗两句《礼》,风从字里过,灯影先伸后回;老人坐在“愿灯”下歇了一歇,歇够了,笑,说“我写了一辈子名字,今日这‘愿’字写得心安。” “以灯惑众,以女乱政”的流言没有再起。市署“回声井”还想吃两口,鼓声却只回了一个“嗯”,像有人在井里打了个哈欠,睡了。 午前,城北的风轻易不过。八风之台上,“东风条”最动。台下那个穿淡青衣的身影又来了一次,站在灯外半步,目光从“愿灯”掠过却不停。 她在灯影旁停了两息,转身时,正对上鸩的目。二人皆未言。她把一包细细的针线放在“风梁”旁,针头收得很细,线头绾成小环。针包上绣一个细细的“月”。 鸩把针包收起,回身入影。她知道,地图上的那个小小的空,已经有人来轻轻按了一指。 —— 黄昏前,卫峥把第三日的账册再晒一次。 太学经籍重修、四门修缮、仓外赈济,三册并列。人围着看,年轻的字、老人的字、快字、慢字,都在上面落了印。印只有一个“愿”。 郭嘉站在远处,不近不远。胸口那只手又掐了一下,他不躲。 痛像一阵风从骨缝里钻进去,又从背后出来。他在这阵风里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鼓,不是弦,是一只细细的木雀在图纸上落下时的那一点“叮”。 他笑了一下,低声道:“月英,谢你。” 他没有把“谢”写成字,也没有把“月英”说给人听。 他只是把“九府工图”的角一折,折出一道细细的“空”,然后将这张图塞进许都的骨里——让它在骨里呼吸,在风里呼吸,在灯与人的影子之间呼吸。 —— 入夜,城灯如常。太学南墙第三盏灯定定地跳了三下,又稳住。 焦尾覆绢,缺弦仍不接。 郭嘉在小院,坐在半盏灯下,把那只木雀放在案边。他把“阅风图”的“空”空着。空,不是缺;空,是留。 留给风,留给人,也留给荆州有女,名曰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