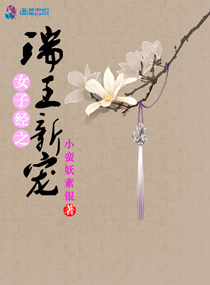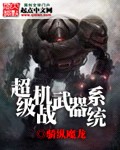凉拌的小黄瓜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崔焕之闭门三日,未曾更衣梳洗。 书房内墨香浓重,七份《灯礼新解》静静躺在紫檀案上,纸页微黄,字迹沉稳如刻。 每一份都加盖私印,封入油纸信囊,由心腹仆从连夜送往江南、荆楚、河东七大学宫。 他不求立时回响,只求这声音能穿破朝堂禁令,落入真正读书人耳中。 可消息尚未出城,安国公府外的长街上已起了异动。 天刚破晓,霜气未散,一队赤足孩童自南而来,约莫十人,皆着粗布短衣,手持竹板,脚步齐整。 为首是个盲童,眼覆黑巾,颈间悬一枚铜铃,铃身细刻柳叶纹,随步轻响,如风拂林梢。 他们列于崔府门前,不跪不拜,只以竹板击节,齐声诵道: “礼在人心不在册,光行千里不须骑。” 声调古拙,节奏分明,像是从久远的乐府深处传来。 巡街吏闻讯赶来,挥鞭欲驱,却见那盲童忽将铃一抬,清音三响,其余孩童立刻止声,静若幽谷。 领头小吏皱眉逼近:“谁教你们来的” 盲童不动,只低声答:“我们是光的脚。” 人群渐聚。 有老儒拄杖上前,听罢泪落满襟:“此音近古乐府……三代之风也。”有人认出铃纹来历,低语四起:“这是江南‘绣议会’的暗记,柳知秋的手笔。” 消息如风,一夜吹过六州。 苏锦黎在鹤影谷收到密报时,正倚窗看雪。 韩砚立于阶下,捧着一卷各地传来的灯诗抄本,眉宇间难掩震动。 “柳知秋三个月走遍十二州,收容失学盲童十六人,亲自授诗、定节、教铃语。如今‘光之行者’已成气候,每至夜半,便有孩童沿街诵灯诗,百姓追听如潮。” 她指尖轻叩窗棂,眸色沉静。 “识字的人怕禁令,不识字的人不怕。他们记不住字,但记得住声音,记得住节奏。这才是最锋利的刀——不是写出来的,是唱出去的。” 她起身,取过朱笔,在舆图上划出七点。 “设‘听铃驿站’,以商盟名义运作,每州一处,专供行者食宿传递。再命匠人在各城灯亭外墙嵌可拆换木板,每日更换百姓手书灯诗,名曰‘灯帖’。” 韩砚迟疑:“若朝廷追查……” “那就让天下人都看见,他们查不过来。”她淡淡道,“一盏灯灭了,还有千百人提笔。你压得住火,压不住话。” 命令下达不过三日,金陵朱雀街便被层层叠叠的灯帖覆满。 白日里看去,千纸翻飞,字迹或工整或歪斜,内容却惊人一致: “你灭一盏,我写百行。” 有孩童踮脚贴上新诗,有老妇颤巍巍写下亡夫姓名,有书生怒书“崔焕之无罪”。 衙役撕一张,便有人补十张;官府派兵值守,百姓便夜里偷偷张贴。 一夜之间,整条长街如披素甲,肃穆如碑林。 与此同时,户部主事崔明远奉太子密令,彻查“灯帖煽众”一案,亲赴扬州查封三处驿站。 他带差役破门而入时,原以为会撞见聚众谋逆之徒。 却不料屋内数十盲童静坐如松,手中竹板轻敲,口中吟诵不断,声浪如潮,竟震得梁上积尘簌簌而落。 “父执礼部时,曾受贿三千金,换举子功名;母家田产二十顷,皆系强占民地……” 突有一童起身,声音清亮,一字一句报出崔家旧案底细,连账目年月都不差分毫。 崔明远脸色骤变:“哪来的野种,敢污蔑朝廷命官!” 那孩子却不惧,只将颈间绣铃高举:“此铃由母亲遗物所铸,她说,错一个字,她死不瞑目。” 门外忽闻锣响。 一声接一声,由远及近。 数百商户持灯列巷,灯笼上写着“漕粮不通,万民同罪”。 为首的米商冷冷道:“今日若抓一童,明日断一船米。” 崔明远被困驿中整整一夜。 窗外诵声不绝,灯影摇曳如海。 他坐在案前,看着桌上一封未拆的家书,终究没敢点灯。 而在宫墙深处,沈知意悄然合上一只青布小袋,袋中装着最新录下的盲童诵诗稿本。 她望了望御书房方向,那里灯火未熄。 风穿过回廊,吹动檐角铜铃。 叮——叮——叮—— 三声为序,如约而至。夜风穿殿,烛火轻晃。 沈知意跪在御书房外的青石阶上,指尖紧攥那卷青布小袋,掌心已沁出薄汗。 她不敢抬头,只听见里头笔锋划纸的沙沙声,久久不歇。 良久,门扉“吱呀”一响,内侍低声道:“娘娘,陛下召你。” 她膝行入内,垂首至地,将布袋高举过顶。 皇帝未接,只道:“念。” 声音清润,逐句展开。 是盲童诵诗录——从《灯礼新解》衍出的四言、五言短章,有讽苛政者,有悼亡者,亦有述百姓日常疾苦之语。 最末一段,竟是崔焕之早年所撰《熄灯论》残句,被编成童谣重唱:“灯灭非为暗,惧光入寒门。” 殿内寂静如渊。 皇帝靠在紫檀椅上,目光落在案前一幅舆图,七点朱砂赫然连成一线,正是“听铃驿站”的布局。 他忽然开口:“他们怎么记得住一字不差,千里传音,岂是孩童所能” 沈知意垂眸,答得平稳:“靠铃声节拍。一句三响,起承转合皆有定律。错一句,铃音即乱,众人自会纠正。这不是记,是刻在骨里的回响。” 皇帝冷笑一声:“好一个‘以声载道’。”他提笔蘸墨,在批阅至半的《国子监考绩簿》上写下一行朱批:“学问不在舌辩,在民心所诵。” 翌日清晨,圣旨下达:崔焕之免去国子监讲经之职,调修《礼乐辑要》,不得参与朝议。 消息传出时,苏锦黎正立于江畔渡口。 深秋黄昏,霜色染衣。 江面雾气浮动,一艘乌篷船泊岸,柳知秋扶着盲童一一登船。 每个孩子怀里都抱着一只木匣,匣中盛满各地百姓手书的灯帖——歪斜的字迹,灼热的名字,未竟的控诉。 他们要去岭南,那里三年未开科考,书院尽毁,民间识字者不足十之一二。 苏锦黎望着那支沉默而坚定的队伍,忽从袖中取出一枚陶铃。 它粗朴无华,既无铜质,也无纹饰,仅在内壁刻了一行细若游丝的小字:“光若能走,何须等待点燃” 她指尖拂过那句话,轻轻一笑,随即抬手,将铃投入江流。 陶铃沉入水底,无声无息。 但对岸山道上,第一支“光之行者”已整队出发。 竹板击节,铜铃轻响,一声接一声,渐行渐远,如同星河流转,河岳移动。 他们带不走火种,却让光自己长出了脚。 风掠过芦苇丛,吹动岸边尚未贴完的灯帖,纸页翻飞,像无数欲飞的魂。 数日后,内府档案房。 裴照站在廊下,看着吏部急令张贴于门侧:“巡守司旧档归档内府,凡涉边政遗文,非旨不得调阅。” 他眉心微动,袖中手指悄然收紧。 昨夜他还曾调阅过一份三十年前的戍边粮册,今日再去,却发现原档已撤,柜中空余编号。 更奇怪的是,据值夜老吏私语,过去三日,已有十七卷边政文书被人提走,登记簿上却无签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