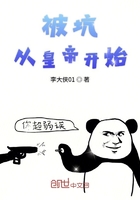凉拌的小黄瓜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子时的风穿过七王府书房窗棂,吹得烛火微微晃动。 苏锦黎合上那本《嘉禾年宗祀辑要》,指尖仍残留着纸页边缘的毛糙触感。 她没再翻看,只是将书轻轻推至案角,仿佛怕惊扰了其中沉睡多年的字句。 但她心里清楚,那一页夹缝里的墨痕不是偶然。 有人曾反复摩挲过这一条——“凡先帝昆仲,虽无嗣承统,若健在者,当授‘奉慈郡王’虚衔,享正一品俸,列祭太庙东序。” 这八个字,足以撬动整个朝堂的根基。 翌日清晨,林砚舟便已伏案三更未眠。 他素来清瘦,眼下青黑如染,手中朱笔却稳如铁铸。 七份誊抄条文整齐叠放在案头,每一份都加盖私印,分别送往内阁、礼部、宗人府。 他不做辩解,不附陈情,只以太常寺博士之职,依典据实呈报。 “礼不可废,名不可僭。”他在最后一份副本旁写下这句话,掷笔起身。 可不到两个时辰,圣谕便至:林砚舟擅传野史、淆乱宗法,贬为皇陵碑文整理使,即刻赴西山履职。 消息传出时,崔礼正在礼部大堂训斥属官。 他拍案冷笑:“一个小小博士,也敢拿几十年前的手抄残本挑战祖制奉慈郡王我大周从无此号!” 他下令追查所有收到条文的官员,严令封存副本,违者以“动摇国本”论处。 但崔礼不知道的是,在他咆哮朝堂的同时,钦天监副使程砚秋已在病榻上提笔写下首份奏报:“昨夜紫气东来,荧惑守心而不动,主宗亲重光,宜复长支名分,以应天和。” 这份奏报由苏锦黎亲自润色,遣词平和,却暗藏机锋。 它不谈权谋,只言天象;不指太子,唯说孝道。 更妙的是,落款时间早于林砚舟递文半日——仿佛冥冥之中,天地先行示警。 紧接着,三位致仕御史联名上疏:“孝治天下,不在虚仪,而在实敬。今有先帝兄长安在,岂可使其布衣终老、祭不得位” 朝野震动。 而坊间,更是悄然流传起一本小册子——《庆元王逸事》。 书肆老板只道是新出的话本,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旧事钩沉:庆元大王年轻时任边关巡查使,替阵亡将士代写家书百余封;寒冬大雪封路,他变卖私产购棉衣三千件,连夜送往前线。 有老兵含泪回忆:“那年我们冻掉了手指,但没人冻死,因为王爷来了。” 短短三日,《庆元王逸事》售出千册,街头巷尾皆议“仁王归来”。 苏锦黎坐在七王府暖阁内,听着程双轻声汇报各地反响,唇角微扬。 她知道,这场仗,打得不是律法,而是人心。 谢云归是在第五日早朝提出动议的。 他站在殿中,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今既有天象示吉、士林陈情、民间颂德,又有古籍佐证,不如交由九卿议政会公决,以彰公允。” 太子党群臣哗然。 他们原以为此事不过是庶务纷争,最多引发几句争议便可压下。 谁知一觉醒来,竟成了满朝热议的焦点。 户部侍郎第一个表态支持:“臣老家在朔州,百姓至今称颂庆元王恩德,祠庙香火不断。”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紧随其后:“名分不定,则礼崩乐坏。今日贬一人,明日削一爵,将来谁敢言正统” 就连一向中立的兵部尚书也低声道:“边军多知其名,若能正位,或可振军心。” 崔礼脸色铁青,环视四周,却发现往日听命于他的几位官员竟低头不语。 他知道,自己已被孤立。 退朝后,他匆匆赶往东宫,脚步急促如奔丧。 而此刻的七王府,苏锦黎正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苍茫天际。 萧澈靠在廊下软轿中,披着玄色狐裘,面色依旧苍白,眼神却亮得惊人。 “你赌赢了。”他低声说。 她回头看他,摇头:“不是我赢了,是我们逼他们不得不选。他们可以否认一条旧例,但挡不住天意、民心、官声三方汇聚。一旦形成势,便是皇帝也不能轻易逆转。” 他轻笑一声,抬手抚过唇边药渍,“接下来,就等那一日了。” 她点头,目光沉静。 夜风又起,檐铃轻响。 远处传来车轮碾过青石的声音,缓慢、坚定,像是某种久违的脚步正缓缓归来。 案几上,《嘉禾年宗祀辑要》静静躺着,翻开的那一页,墨迹斑驳,却字字清晰。 议政当日,天光微明,南书房外青石阶上已聚满朝臣。 九卿议政会向来只在重大国事时召开,今日却因一纸旧律、一位隐居三十年的亲王而重启,人人神色凝重,低语如潮。 庆元大王的青帷车缓缓停在宫门外。 车帘掀开,他步下踏凳,一身素金襕袍在晨风中轻扬,虽无绣纹加身,却自有威仪凛然。 白发如雪,脊背笔直,仿佛一道从旧时光里走出的影子,沉静地落在这片喧嚣朝堂之上。 林砚舟立于阶前,手中捧着黄绫诏书,指尖仍有些微颤。 三日前他还是被贬西山的罪官,如今却站在这里,代表礼法宣读敕命。 他深吸一口气,展开圣旨,声音清越而坚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先帝昆仲,庆元大王年高德劭,仁名远播,依《嘉禾年宗祀辑要》旧制,特授‘奉慈郡王’虚衔,享正一品俸禄,列祭太庙东序,以彰孝治之本……” “且慢!”崔礼猛然出列,袖袍翻飞,“郡王封号,历来由天子亲授玺绶,岂能由会议定夺此例一开,宗法何存” 殿内顿时一片寂静。 众人目光交汇,皆知这一问直指权力核心——若封爵可由群臣公议决定,那皇权是否还能独断 就在这死寂之中,萧澈缓缓抬眸。 他坐在轮舆之上,面色苍白如纸,声音却不疾不徐,像一把钝刀切入骨缝:“那么,请问尚书大人——当年先帝登基时,太子可曾亲手接过玉圭还是由摄政王代行” 一句话,如雷贯耳。 崔礼浑身一震,脸色骤变。 那是先帝早年病重、太子年幼时的旧事,本属宫廷秘辛,极少公开提及。 如今被萧澈当众点破,无异于揭了太子党最不愿示人的短处:你们口口声声讲礼法,可当年自己就坏了规矩。 满堂鸦雀无声。有人低头避视,有人嘴角微动,终是无人应和崔礼。 林砚舟趁势继续宣读,一字一句落地有声。 待到最后“钦此”出口,九卿之中已有七人起身拱手称贺,连一向谨慎的户部尚书也颔首默许。 敕命通过。 当夜,庆元大王在府中设宴答谢诸位支持者。 席间酒不过三巡,言不及奢靡,唯有敬意深重。 宴至尾声,老人独留林砚舟于偏厅,屏退左右。 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章,边缘磨损严重,火漆印早已褪色,唯有一个“安”字依稀可辨。 “这是我替戍卒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上的印。”他低声说道,目光落在那小小印记上,像是穿越了风雪边关,“你说的那些事……我没忘。” 林砚舟喉头一紧,竟说不出话来。 庆元大王抬眼看他,眼中泛起水光:“这江山要是早些听你们的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 庭院中,苏锦黎独自立于月下。 晚风拂面,她望着宫城方向,忽听得远处钟楼传来十二响钟声——这一次,不再是乱敲的警示,而是准时准点的报更。 她轻轻吐出一口气,唇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现在,轮到我们定规矩了。” 而在东宫深处,烛火昏暗。 太子将一份名单撕得粉碎,纸屑纷飞如雪。 他盯着地上残片,咬牙切齿,一字一顿:“苏锦黎……你以为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