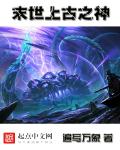凉拌的小黄瓜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尚书府禁声三日,宫中却传出其夜半再度呓语,竟被贴身小厮录于纸笺:“贞和九年冬,枢密使亲携金箱入礼部,内装‘定音尺’三枚——实为铅条镀银。” 这行字辗转传入都察院耳目时,天光尚在云层后挣扎。 裴文昭正坐在案前,手中一卷泛黄账册翻至中间一页,指尖停在一笔“特制律器,支银三千两”的记录上。 他盯着那几个字许久,忽然轻笑一声,将纸笺与账册并排压在镇纸下。 不是巧合。 先帝年间,工造司所铸礼器皆以铜锡合金为主材,尤重编钟、定音尺等礼乐重器的声准纯正。 可三千两银换来的若是铅芯镀银的假物,那不止是贪墨,更是对天地祖宗的欺瞒。 他合上账册,唤来随从:“去查十年前北境各军镇配发的祭旗铜钟,有没有留存实物。” 当夜,代州总管魏承业接到一封密信。 信封无印,只有一道朱砂画线,象征紧急军情等级。 他拆开一看,脸色骤变。 附言短短一句:“边军若曾用此钟祭旗,便是欺神辱卒。” 他当即命人取来库中一口熔毁旧钟剖开查验,果见内部填充大块暗沉铅块。 再翻出十年前北境冬祭鼓谱残卷,对照现存编钟音高,主调竟低了整整半律。 “怪道那时将士听令迟缓——”魏承业怒拍案几,声音震得烛火晃动,“原来战鼓都走了调!” 音不准,则令不达;令不达,则阵不成。 一场战役的溃败,或许并非因将帅无能,而是起于一座走调的钟。 他当场修书一封直呈兵部,要求彻查历年配发礼器材质,并随信附上那口剖开的废钟。 消息传回京中,兵部连夜报备内阁,称此事“或涉先帝定制”,措辞谨慎却难掩震动。 而此时,安国公府偏院一间静室里,苏锦黎正听着韩四娘低声禀报。 “裴大人已派人暗访太常寺老乐正,有人记得当年验收时觉音色浑浊,但不敢言。” “魏总管那一口破钟送进兵部时,守门官差点拒收,说是‘污损朝廷礼器’。” “还有……陈老昨日又收了两名弟子,都是国子监生员,说想学‘不靠官印也能辨真音的本事’。” 苏锦黎指尖轻轻敲着茶盏边缘,瓷器发出细微清响,如滴水入潭。 她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忽问:“陈老近日可还收徒” “回主子,昨日又有两名国子监生员登门求教,说是‘想学不靠官印也能辨真音的本事’。” 她微微颔首,唇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人心动了。 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自下而上的觉醒。 当读书人不再盲信官文书印,开始追问一声钟鸣是否纯粹,那便是旧秩序崩塌的第一道裂痕。 她起身走到书案前,取出一部新制《正音通考》初稿,翻开最后一页,在空白处亲笔添注一条:凡律不合者,不论出处,皆伪。 八个字,斩钉截铁。 这不是学术之争,是道统之辩。 若连最根本的“音准”都可以被权势扭曲,那礼何存 法何依 国何以为国 她将书交予韩四娘:“送去沈协理处,请她明日持书赴国子监,名义为赠典讲学。” 韩四娘顿了顿:“可要备车马仪仗” “不必。”苏锦黎摇头,“越低调越好。但她必须带一口钟——由盲童亲手校准的新铸小钟。” 韩四娘退下后,她独自立于窗前,看着晨雾弥漫庭院。 萧澈昨夜未归,据说是皇帝召见议事,至今未散。 她知道,这场风暴已逼近中枢。 礼部尚书疯也似的呓语,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真正深埋海底的,是整个先帝朝以来,礼、工、兵三部与枢密院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 而如今,证据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像无数细流终将汇成洪涛。 她并不急于掀桌。 有时候,最有力的打击,是让对手自己站出来,跪下。 数日后,沈琅抵达国子监外。 清晨薄阳洒在青砖地上,她并未走向讲堂正门,而是转身走向监中僻静一隅——那里立着一块斑驳石碑,刻着“音魂”二字,相传为百年前一代乐宗手书,历代乐官祭拜之所。 她在碑侧设席铺毯,摆上那部《正音通考》,又令人抬来一口小巧铜钟,置于蒲团之上。 诸儒陆续到来,有人皱眉,有人疑惑,却无人离去。 沈琅静坐良久,直至众人落定。 然后,她抬手,示意身边侍从执槌。 一口钟,一人,一槌。 钟声独鸣三响,清越悠远,穿林透雾,仿佛涤尽尘世虚言。 余韵未绝之时,她缓缓起身。 沈琅至监中不坐堂前,反设席于“音魂碑”侧,请诸儒闭目听钟。 晨光微斜,青石板上浮着一层薄霜。 她未着官服,只穿一袭素色深衣,发间无簪,腕上无环,唯有一口小钟静置于蒲团之上,铜身尚未经风沙磨蚀,泛着新铸的温润光泽。 那钟由京郊盲童坊的孩童亲手校音——那些自幼失明的孩子,耳朵比常人更敏,心也更净。 他们听不出权势的高低,只听得清音律的偏正。 “请诸公闭目。”沈琅声音不高,却穿透了人群间的低语。 众人迟疑片刻,终究依言阖眼。 一声槌响。 钟鸣初起,如泉击寒潭,清冽入骨。 第二声,悠然延展,似云出幽谷,不疾不缓。 第三声落时,余韵袅袅,竟引得林间宿鸟惊飞数只。 万籁俱寂。 沈琅缓缓起身,立于碑侧,目光扫过一张张或苍老、或年轻的脸庞,最终落在最前方那位白发萧然的老乐正身上。 “此音合《周礼大司乐》所载黄钟之均。”她的声音平静,却字字如锤,“而今太常寺库存‘正声’,实则偏羽位一丝——请问诸公,是经书错了,还是钟错了” 无人应答。风停树静,连呼吸都仿佛被压住。 良久,那老乐正颤巍巍站起,双手捧出一支玉律管,据说是祖上传下,历经三代帝王祭祀所用。 他嘴唇哆嗦,将玉管对准唇边,轻轻一吹,再与记忆中的钟声对照——忽然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我……我侍奉三代帝王……”他哽咽难言,老泪纵横,“每年春祭冬祀,调音校律,从不敢懈怠……可原来……原来我们一直吹的是假调。” 话音落下,如同一道裂痕自地面蔓延开来。 七名来自太常寺的乐正相继离席,徒步走向正音局。 当夜,月色冷清。 七人跪于正音局门前石阶,双手高举檀木匣,内盛历代传承的“御定律谱”原本。 守门弟子吓得几乎跌倒,欲奔去通报,却被檐下一抹身影拦住。 沈琅站在廊下,披着一件旧斗篷,静静望着这七位曾经高居庙堂的乐官。 她没有立刻接谱,也没有命人搀扶,只是在沉默中踱步而出,俯视着那斑驳匣盖。 “诸位可知,”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风拂过瓦当,“百姓为何宁信窑工,不信庙堂” 老乐正伏地不起,额头触石,声音破碎:“因为我们……早就忘了怎么听真声音。” 那一刻,沈琅没再说话。 她只是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看见夹页之间密布红笔批注——哪些音需“上提半厘”,哪些律要“压低三毫”,皆有定例。 不是修正,是篡改;不是误差,是谎言。 她合上匣子,转身走入厅堂,将它置于案首,如供神明。 同一时刻,七王府偏殿。 苏锦黎手持镊子,将一枚极细的铜屑嵌入新钟悬钮的凹槽之中。 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暗交错。 韩四娘立于身后,低声问:“主子,真能响吗” “能。”苏锦黎淡淡道,“只要有人愿意听。” 她抬头看向庭院深处那口悬挂多日的测音钟——忽然,钟钮轻震,钟身无风自动,一声清越骤然划破夜空,仿佛天地自行校准。 她闭了闭眼。 这不是胜利。 这是崩塌开始后的第一声回响。 而在千里之外的洛阳,一条狭窄潮湿的贫民巷中,一名少女蜷缩在熄灭的灶台边,指尖沾着炭灰,在斑驳墙面上反复描画一组奇异纹路——线条交错如钟纽盘绕,又似音波流转。 邻人探头问她在做什么,她只是摇头,喃喃低语: “爹临死前说,这图能救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