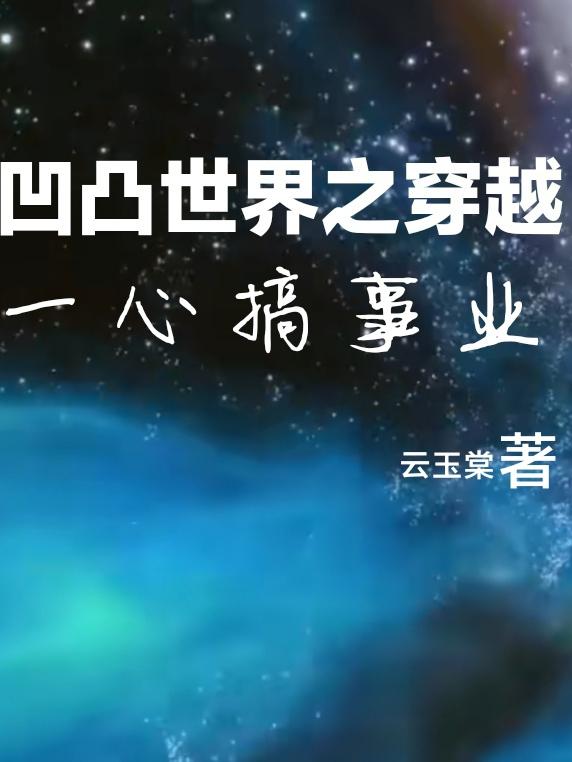贾闲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窗外的梧桐叶从嫩绿变为深绿,夏季悄然临近。林墨在学业、重大项目与特殊任务交织的网中从容穿行,手中的蓝图日益清晰,心中的道路也愈发坚定。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那从图纸走向现实的、更为波澜壮阔的建设阶段。 春深夏浅,水木大学的校园里,梧桐华盖亭亭,投下浓密的绿荫。然而,这片往日里纯粹萦绕着书卷气息的园地,近日却悄然混入了一些不同的声响。 并非朗朗书声,也非辩论喧嚣,而是来自一些穿着工装、身影忙碌的工人师傅。他们或在教学楼旁的空地上支起简易工棚,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什么; 或在老师的陪同下,穿梭于实验室与实习工厂之间,操弄着学生们平日更多是在图纸上接触的机床设备。 一股名为“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新风,已然吹进了这所顶尖学府。作为全国高校试点推进的重点,水木大学率先在大四年级开始了探索。 具体的“三三制”或“四四制”学习模式细则尚在讨论,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精神已迅速落地。课程表被重新调整,大量的课时被直接安排到了对口的企业和车间。 对林墨而言,这项政策的出台,几乎是为他量身打造。他无需再为协调项目与学业的时间而额外申请,新的教学安排自然将他每周的三到四天固定在了国营木器一厂。 他如同鱼儿入了水,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联合体的测绘与设计工作中。 厂区里,常能看到他带着图纸,时而凝神远眺整体布局,时而又蹲下身,用卷尺仔细测量着某个角落的尺寸。他那专注的神情和精准的指令,让厂里的老工人们都啧啧称奇。 “嘿,你们瞧瞧小林工,”一个老师傅端着搪瓷缸,对旁边休息的工友笑道,“我看呐,咱们这厂子里犄角旮旯埋了几根管子,哪个阀门年头久了有点渗漏,怕是都没他清楚!” 旁边有人附和:“谁说不是呢!感觉他比咱们这些在厂里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还门儿清!” 被指派协助林墨进行更精细测绘的青年技术员小陈和小李,更是感触颇深。一次,为了确认一条地下废弃管道的精确走向,林墨带着他们几乎翻遍了厂档案室所有的老图纸,又沿着疑似路径反复勘测。 “林工,这都找了大半天了,也许早就填实了呢”小李擦着汗,有些气馁。 林墨头也没抬,手指拂过地面一处几乎难以察觉的轻微沉降痕迹,语气肯定:“不对,看这土质的细微差别和沉降线,下面肯定有东西。” “记录显示这条管道是建厂初期临时铺设的,后来新系统启用就废弃了,但图纸标注模糊。不找准它,我们新车间的基础打下去可能会有隐患。” 他站起身,目光锐利地扫过四周,最终定格在远处一棵老槐树下:“去那边看看,按照总图坐标和地势坡度,出口应该在那个方向。” 几人赶到槐树下,果然在一丛茂盛的杂草后,发现了一个被石板半掩的、早已锈蚀的管道出口。小陈和小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由衷的佩服。 “林工,我算是服了!”小陈竖起大拇指,“您这眼睛,真是比探雷器还准!厂子周边哪里埋了什么东西,怕是真逃不过您的眼睛。” 林墨只是淡淡一笑,在本子上仔细标注好位置:“图纸是死的,现场是活的。多做功课,多观察,总能找到线索。走吧,下一个点。” “半工读”的春风吹拂校园,也带来了另一道风景——一批来自各大工厂、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被请进了水木大学的课堂和实习车间。他们带来的,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数十年摸爬滚打积累下的实战经验和手上绝活。 轧钢厂的易中海和刘海中,也在这股风潮中,披挂上阵,成为了某些大学的“临时教习”。 刘海中对此可谓是志得意满,精神焕发。每次从水木大学讲完课回到四合院,他那挺起的胸膛都恨不得再高上两分。 “哼,以前总觉得大学生多了不起,鼻孔朝天。”他在院里的水池边,一边哗啦啦地洗着手,一边对着围拢过来的几个邻居高谈阔论。 “现在怎么样还不是得乖乖坐在下面,听我老刘讲课!我让他们敲一个标准件,那手抖的,跟得了鸡爪疯似的!” 他尤其得意于自己资助的那个姓蓝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这更让他产生了一种“大学生也不过如此”的优越感。“看看,要不是我老刘当初拉他一把,他能有今天这说明啥说明关键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人提携!光会死读书,不行!” 与他相比,易中海的态度则显得沉稳甚至有些凝重。他同样认真备课,在实习车间里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们操作钳台,讲解如何凭手感判断加工精度。 但站在水木大学宽敞明亮的实习车间里,看着那些虽然稚嫩却充满求知欲的年轻面孔,以及车间里那些比轧钢厂更先进、更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位八级钳工的心中,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一次课后,他难得地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里面仍在埋头练习的学生,对一同回来的刘海中感叹道。 “老刘啊,你看这些机器,精度越来越高,自动化程度也在提升。我琢磨着,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多现在需要低级工、甚至中级工反复操作的工序,将来可能一台机器就能搞定,而且干得更好、更快。” 刘海中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老易,你就是想太多!机器再好,那也得人来开、人来修不是咱们的手艺,那是机器能替代的” 易中海微微摇头,没有争辩,但眼神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看到了技术进步的洪流,也隐约感觉到,固守现有的手艺,或许并非长久之计。 五月来临,天气渐热,四合院里的那棵老槐树也撑开了如盖的浓荫,成了众人纳凉、闲聊的好去处。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股不同于往年的气氛,也开始在这方小小的院落里弥漫开来。 报纸上的社论语调愈发高昂,广播里的内容也更加尖锐,一些新的名词和口号,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言谈中。更让普通工人们心头震动的是,最近轧钢厂乃至其他单位,都传出了一些消息。 某某车间的主任,因为工人反映他搞“物质刺激”、脱离群众,被停了职,正在写检查;某某科室的股长,因为对工人态度粗暴,也被检查,灰头土脸…… 这些发生在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像一块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刘海中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这天晚上,刘海中又在槐树下组织“帮学”。他手里拿着份《工人日报》,上面正好刊登了一篇关于某工厂干部因作风问题被工人批评、上级处理的消息。他念得格外起劲,声音都比平时洪亮了几分。 念完后,他放下报纸,环视一圈听得愣神的邻居,用力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一种洞悉内情的神气,压低声音说道:“大伙儿都听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叫啥这就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往前凑了凑,仿佛要分享什么了不得的发现:“以前呐,咱们觉得那些坐办公室的、当个小领导的,多了不起!说话拿腔拿调,走路都带着风。嘿,现在怎么样”他嗤笑一声,手指点着报纸,“还不是说下来就下来!工人兄弟提了意见,上面就得处理!这说明啥” 他自问自答,语气越来越兴奋:“说明啊,这世道真是在变!工人的地位,那是实实在在地提高!咱们工人阶级,现在说话是管用的!” 这个认知,让刘海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躁动。他过去削尖脑袋想当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官威”的敬畏和羡慕,觉得那是人上人。 可现在,他亲眼看到不少平日里在他眼中高高在上的基层领导,因为工人反映的情况就被停职、靠边站,那种神秘感和优越感在他心中骤然破碎了。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关键还得看根子正不正,思想红不红,跟不跟得上形势!”刘海中得出了新的结论,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找到捷径的光芒。” “他似乎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过去论资排辈、更“革命”、更快速的上升通道——积极表现,紧跟运动,反映问题,证明自己的“觉悟”! 这种新发现的“希望”,让他参与政治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在院里组织学习,在轧钢厂里,他也开始更加留意各种风声,偶尔在小组学习会上,也会试着按照报纸上的调子,对生产管理提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虽然往往不得要领,但他那种突然积极起来的姿态,还是让不少老工友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