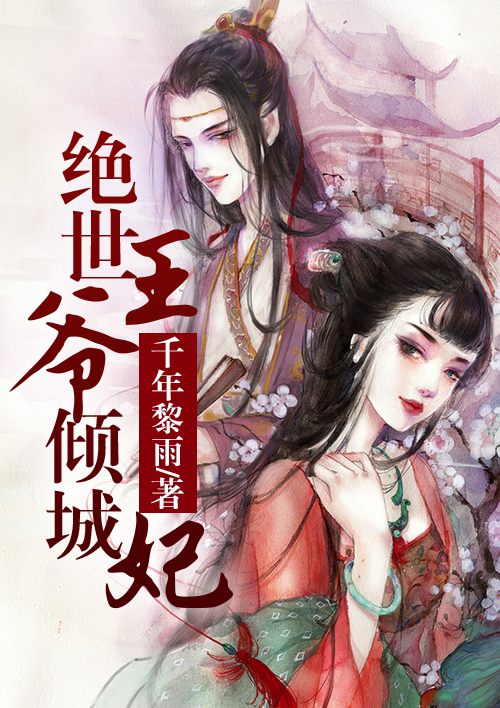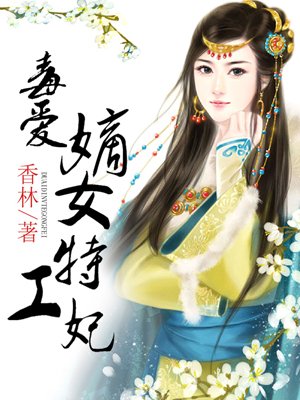牛熊随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张伟的目光落在李明身上,他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这个案子的困惑与不平。 他点了点头,跟着李明走进了律师咨询室。 咨询室内,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带着些许愁苦与倔强的老人正襟危坐。 他身旁放着一根盲杖,双手不安地交叠在膝上。 老人姓姚,叫姚志军。 李明简单介绍了一下,张伟很快便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姚大爷,四级视力残疾,在江城生活了大半辈子。 那天,他如往常一样,拄着盲杖,走在专为盲人铺设的盲道上。 前方一个中年男人,原本同向行走。 可就在姚大爷靠近时,那男人毫无征兆地,突然一个急转身,打算往回走。 姚大爷根本来不及反应。 两人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 结果,那个转身的男人摔倒在地,造成了桡骨远端骨折。 男人将姚大爷告上了法庭。 一审法院的判决,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法院认为,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人士,在公共道路上行走时,未能尽到与前方行人保持安全距离的义务。 因此,判处姚大爷承担70%的责任。 赔偿对方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两万六千余元。 张伟听完,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这判决,确实透着一股子荒唐劲儿。 他看向姚大爷,老人的脸上写满了委屈与不甘。 张伟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关于视力残疾分级的相关法律知识。 视力残疾,通常分为四级。 一级,是最严重的,属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无光感。 二级,也属于重度视力残疾,可能仅存光感,或者仅能感知到眼前晃动的手指,视野半径小于5度。这样的人,在法律上通常会被直接认定为盲人。 三级,属于中度视力残疾,最佳矫正视力可能在0.05到0.1之间,视野半径小于10度。他们能模糊地感知物体的轮廓,但辨识细节极为困难。 而姚大爷的四级视力残疾,是分级中最轻的一档。 最佳矫正视力可能在0.1到0.3之间,或者视野半径小于20度。 这意味着,姚大爷并非完全看不见。 他或许能勉强分辨出道路的大致走向,能感知到前方有模糊的人影或障碍物,就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世界。 但要说清晰视物,或者在复杂环境下快速反应,那是绝无可能的。 关键点在于,法律上,通常只有二级及以上的视力残疾人士,才会被严格意义上认定为“盲人”,从而在某些注意义务上有所豁免。 而四级视力残疾,虽然生活诸多不便,但在法律层面,行路时依旧被认为需要承担一定的观察义务。 这规定,在实际情况中,对于许多四级视残者而言,几乎是苛求。 但法律条文,就是这么冰冷而刻板地存在着。 张伟内心也不禁叹了口气。 他不是立法者,改变不了这操蛋的规定。 他能做的,只有在现有框架下,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张伟声音温和,尽量安抚道:“姚大爷,您先别激动。您这个情况,我们详细了解了。” 姚大爷情绪有些激动起来,布满皱纹的脸上涨起一层红色。 “张律师!我真的是冤枉啊!” “我一个眼睛不好的人,规规矩矩走在盲道上!” “是他突然转身撞过来的!我哪儿看得清我哪儿躲得开” “凭什么要我赔钱还要我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老人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 张伟看着姚大爷激动得通红的脸庞,内心充满了无奈。 是啊,从朴素的情感和道义上讲,姚大爷的话句句在理。 一个视力有障碍的老人,走在专门为他们铺设的盲道上,却被一个正常行走的、突然转向的人撞伤,反倒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觉得憋屈。 但是,法律的逻辑,往往和普通人的情感认知存在偏差。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在脑海中对这个案件进行解构。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这就是法律上的“过失相抵”原则。 这个原则的构成要素有三点。 第一,双过错并存性。 这意味着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也就是那个突然转身的行人和姚大爷,都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 行人突然转身,未尽到对盲道使用者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 而姚大爷作为四级视残者,在法律上仍负有部分观察义务,他未能及时避让,也可能被认为未尽到保持安全距离的注意义务。 第二,原因力交织性。 双方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行人的突然转身,是直接诱因。 姚大爷作为四级盲残,未达到认定盲人标准,需要承担观察义务。 在此情况下,姚大爷未能有效避让,也是导致碰撞发生的因素之一。 两者相互作用,才造成了行人摔倒受伤的结果。 第三,责任可量化性。 法庭可以根据双方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以及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进行责任的划分。 一审法院判决姚大爷承担70%的责任,正是基于对这些过错因素的量化评估。 虽然在情理上让人难以接受,但在法理层面,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谁让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冰冷,且不近人情。 张伟沉吟片刻。 如果硬要打这个二审,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 突破口,就在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二十二条! 该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无障碍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 盲道,正是为保障视力残疾人安全、便捷出行而设置的无障碍设施。 它承载的,是视力残疾者能够安心通行的法律保障。 那个正常行走的男人,在盲道上突然急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擅自改变盲道用途”的行为。 他将原本专属于盲人安全通行的道路,变成了自己可以随意转向、不顾后果的“普通路段”。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盲道的使用规则,更直接增加了姚大爷这种视力残疾人士的通行风险。 可以大胆主张,正是对方这种改变盲道使用用途的过错行为,才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他的过错,远大于姚大爷在视力受限情况下,未能“及时避让”的所谓过错。 张伟脑中飞速盘算着。 但是,他也清楚,这种案件,法理的天平往往会不自觉地向“结果更严重”的一方,也就是受伤的一方倾斜。 虽然在常理认知中,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者,无疑是弱势群体。 可是在法庭上,那个摔倒受伤,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和各项费用单据的行人,在法官眼中,可能就成了需要“优先保护”的受害者。 打二审,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彻底翻案,判姚大爷无责。 从法理上看,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并非天方夜谭。 但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更大概率的结果,是二审法院对责任比例进行重新划分。 比如,将姚大爷的主责,改为次责,甚至同等责任。 这样一来,赔偿金额确实能减少一部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个案子的总赔偿金额是两万六千元。 即便责任比例大幅降低,比如从70%降到30%,姚大爷也还需要支付近一万两千元。 少赔的这一万多块,能覆盖律师费吗 还有姚大爷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呢 这笔账算下来,对姚大爷而言,未必划算。 张伟的眉头,锁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