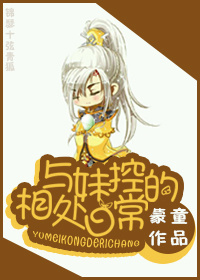湘水湾耕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刘克范显然也感受到了这无形的压力与越来越近的威胁。明德学堂并未因流言和傅鉴飞的忧虑而沉寂,相反,一种更加紧张、更加内敛、同时也更加炽烈的气氛在师生间弥漫开来。 大礼堂里激越的歌声和整齐的操练呼号并未断绝,但大课宣讲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化整为零的小组学习。桂生、谢明玉和几个思想最为活跃、行动最可靠的学生核心,常常在晚课后被刘克范叫到他那间堆满书籍的狭小宿舍兼办公室里。窗户紧闭,厚布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在书桌上点一盏昏黄的小台灯,将几颗紧凑的脑袋投射在墙壁上,如同地下秘密结社的场景。油灯的火苗被刻意捻得很小,只够勉强照亮桌上的文稿。 室内闷热而烟雾缭绕,混杂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和旧书的霉味。刘克范眼神锐利如鹰,压低了声音,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沉浑有力: “同志们,”他用了这个特殊的称谓,让围坐的桂生、谢明玉等人心头一凛,腰背下意识地挺得更直。“外面的风声紧得很。周荫人这头豺狼在汀州扩军备战,搜刮无度。城里的地头蛇、老学究们也嗅着味了,巴不得把我们这‘赤化窝点’掀个底朝天。斗争环境更复杂了,我们更要沉住气,更要讲方法!” 他拿起一张油墨未干的传单样稿,标题是《告闽西工农书》。“光喊口号不行,要戳到痛处!‘耕者有其田’——这口号好,但怎么实现要告诉佃农,土地是你们开垦的,汗水是你们浇灌的,那巧立名目的‘押租’、‘预租’、‘大斗进小斗出’,就是地主刮你们骨头的刀!要告诉挑夫苦力,码头、矿山的血汗钱,凭什么被把头抽走大半凭什么你们累死在矿洞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他手指有力地敲击着桌面,每一下都像敲在听者的心上。 桂生听着,胸脯剧烈起伏,眼里的火焰燃烧得更旺。他想起了自家被山洪冲垮的薄田,想起了爹娘衰老佝偻的身影和三个姐姐被迫远嫁的泪眼。谢先生则飞快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要点,笔尖沙沙作响。 “组织!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刘克范斩钉截铁,“像桂生、阿木(另一个矿工子弟)这样的,你们有家人在乡下,在矿上,这就是根基!回去,把乡亲们的苦处一条条记在心里!帮他们写状子,算明白账!让他们知道,不是命该如此!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串联起来,三户、五户,十户……人数就是力量!告诉他们,南方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党,为他们撑腰!” 他又转向谢先生和另一个识文断字的学生:“小谢,你们的任务更重。把《告工农书》的核心意思,用最朴素、最贴近他们的话写出来。不要文绉绉,要像拉家常,像诉苦!再想办法刻成蜡版,油印出来。要快,要隐秘!只有文字才能突破山水的阻隔,把火种撒出去!” “校长,放心!我们几个人轮流刻版,夜深人静时印,天亮前藏好!”谢先生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武器……”刘克范的目光扫过桂生等几个体格健壮的学生,“光靠锄头扁担不行。我们要有准备。钟先生那边……嗯,有些门路。过几日,会有一些东西送到学堂后面柴房的地窖里。桂生,你带几个绝对可靠的,负责接收、藏好。要万无一失!那些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示人!它们是最后保命的根,也是将来砸碎锁链的铁锤!”话虽隐晦,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了那“东西”指的是什么,一股寒意夹杂着莫名的兴奋从脊背窜起。 “记住!”刘克范的声音陡然压低,带着铁一般的冷硬和警告,“从现在起,一言一行,都要格外小心!敌人有枪有炮,有狗鼻子!任何人被抓了,宁可死,也绝不能吐露半点实情!要保护好组织,保护好我们的人!保护好我们辛苦积攒的这点力量!”昏黄的灯光下,他脸上每一道深刻的皱纹都如同刀刻,目光灼灼,扫过每一张年轻而紧张的脸庞,那眼神里是沉重的嘱托,是无声的誓言。 桂生用力挺直腰板,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咕哝:“校长,我桂生用命担保!谁要是孬种,天打雷劈!”其他几人也都重重地点头,神情肃穆而决然。 南芝依旧在她那方寸的档案室里忙碌。然而,她敏锐地察觉到,近期需要她整理归档的纸张,内容愈发地“烫手”。 一份份新刻印出来的传单和小册子被秘密送到她的桌上。纸张粗糙,油墨时常洇开,字迹也因刻版者的紧张而略显潦草,但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怒火却几乎要灼穿纸背: > “汀江两岸的父老乡亲们!睁开眼看一看!是谁在吸我们的血是周荫人!是张毅!是骑在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军阀地主!……” > “长工佃户兄弟们!算一算账吧!我们流尽血汗打下的粮食,七成进了地主老财的粮仓!他们住高楼大厦,我们住破屋漏房!这是什么世道!” > “工友们!把头、监工凭什么抽走我们一半的血汗钱凭什么像使唤牛马一样鞭打我们团结起来!抱成团!成立我们工人自己的团体!拒交苛捐杂税!要求八小时工作!……” > “看看南方!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北伐反帝反封建!他们是工农的军队!他们打到哪里,哪里的工农就挺直腰杆!现在,工农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已经在一些地方建立起来了!那是我们当家作主的政府!……” 这些直白、尖锐,甚至带着煽动性的文字,猛烈地冲击着南芝的认知。她看到“苏维埃”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含义也愈发清晰具体——不再是刘克范激情演讲中那个模糊的理想国轮廓,而是与“工农兵代表会议”、“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工厂”这些具体诉求紧密相连的、活生生的政权形式。 还有一份标题触目惊心的文件,用粗大的字体写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摘要)》。其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等字句被重重圈出。旁边附着钟先生用工整小楷写的批注:“此为我党(指cp)主张之核心体现,亦是当前革命之总纲。须深刻领会,广为宣传。” 每次整理这些材料,南芝都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她如同捧着一块块烧红的烙铁,动作愈发谨慎小心。在登记簿上写下这些标题时,她甚至下意识地侧耳倾听门外是否有异动。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真正的引火线!被点燃的,将是整个闽西! 就在这天深夜,万籁俱寂。一阵极其轻微、如同鼠啮的叩门声在档案室的后窗响起,规律而急促。南芝心头一紧,放下手中刚盖好编号的传单,屏住呼吸走到窗边。窗外一片漆黑。她轻轻推开一条缝隙。 桂生那张焦急又紧张的脸出现在黑暗中,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在月光下闪着微光。他压低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痛楚喘息:“南芝妹妹!快……快开门!阿木他……他不行了!” 南芝一惊,借着窗棂透进的微弱月光,才看清桂生背上还背着一个人影——正是那个矿工子弟阿木!阿木的头无力地耷拉在桂生肩头,身上那件洗旧的靛蓝学生装被大片深色的、黏稠的液体浸透,散发出浓重的血腥味!一条腿软绵绵地垂着,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因为剧痛而不停地哆嗦着,发出微弱的、压抑的呻吟。 “怎么回事!”南芝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压得极低,心脏狂跳起来。 “在……在城西乱石坡……”谢明玉喘着粗气,声音抖得厉害,“我们……我们按校长吩咐,去接……接‘东西’……回来路上,碰……碰上了巡夜的税警队!他们……他们想搜身!阿木护着包袱……被……被那狗腿子当胸一脚踹下了陡坡!腿……腿怕是折了!还……还有内伤!我们不敢去诊所,怕……怕被查问……”他眼中充满了愤怒,泪水混着汗水流下。 包袱!东西!南芝瞬间明白了桂生话语中的隐晦所指。那所谓的“东西”,是武器!是刘校长口中“最后保命的根”和“砸碎锁链的铁锤”!阿木是为了保护它而受的重伤!一股寒意夹杂着莫名的悲壮感瞬间攫住了她。 她来不及多想,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拉开后窗的插销:“快!扶他进来!”桂生咬着牙,拼尽力气将几乎昏迷的阿木从窗口拖了进来。南芝迅速关紧窗户,拉上窗帘。 档案室里弥漫开血腥气。阿木瘫软在地,呼吸微弱,那条受伤的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谢明玉蹲在他身边,手足无措,急得直掉眼泪:“南芝小妹!怎么办不能……不能让他死啊!” 南芝看着阿木惨白的脸,看着他身上那件被血染透的靛蓝学生装——那是明德学堂的象征。 “桂生哥,你学过医多年,我配合你,看如何做。” 南芝果断地低声道,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然。“需要的药去找济仁堂,或者找傅医生出诊。” 南芝这个时候似乎顿悟,那些“赤化”的油印纸,此刻在她心中,已不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与眼前这条年轻、鲜活、正被残酷现实撕裂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沉甸甸的现实! 武所城的晨雾还未散尽,城南十字街口的电灯杆上,那盏新装的灯泡已经亮了三天。黄澄澄的光裹着细碎的灰尘,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朦胧的光晕,引得早起的挑水夫、卖菜佣驻足张望。卖豆浆的王二麻子舀着碗里的热浆,冲旁边扯着嗓子喊:“老张你瞅瞅!这洋灯比咱家那盏煤油灯亮堂多了,连瓦檐上的霜花都照得清!” 可这光亮照不进百姓的灶房。城西张庄的李阿婆蹲在漏风的土屋里,就着豆大的油灯给咳血的孙儿熬草药。她的儿子被拉去当壮丁三年未归,儿媳改嫁,只剩祖孙俩守着半亩薄田——那地早被城里的王记米行老板王怀仁以“抵债”为由强占,如今连糊口的口粮都要靠挖野菜。“这洋灯再亮,能照见俺孙儿碗里的米粒么”她抹着泪,将最后一把柴火塞进灶膛。 此时的城关济仁堂药铺里,傅鉴飞正用听诊器给前来看病的富商陈掌柜听心肺。今天他似乎有点心不焉。他不时想到了今早从广州寄来的那本《汀雷》杂志。 “傅先生,您这脉诊得够久的啊!”陈掌柜不满地抽回手腕,“我这心口闷,怕不是中了邪听说最近城里来了几个‘赤党分子’,是不是他们做法害人哩!” 傅鉴飞不动声色地收起听诊器:“陈掌柜这是劳神过度,我开副安神的方子便是。”待送走这位“体面人”,他才从柜台暗格摸出那本杂志。封面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红字被晨露浸得发软,内页却密密麻麻印着北伐军的捷报、农民抗租的新闻,还有篇《论工农的力量》的文章,写着“中国四万万同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那些弯着腰种地的、流着汗做工的”。 “这道理,咱武所的老百姓有几能懂”傅鉴飞叹了口气,目光扫过药铺后堂堆着的草药包——最底下压着一沓没送出去的账单,全是穷苦人家赊的药钱,最长的已经欠了两年。 十月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明德学校的教室时,校长刘克范正站在讲台上讲《论语》。这位穿着藏青长衫、戴着圆片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武所城最有学问的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去福州师范进修过,回乡后办了这所新式学堂,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讲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刘克范刚讲完课,放下粉笔,想走到学生中聊聊。 “先生,广州来信了!”教室里一阵骚动。见校役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信,“是修焕堂先生广州寄来的,说是托人带回来的!” 教室后排立刻挤过来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为首的叫桂生,原来是傅鉴飞药铺的学徒,因算账快、人机灵,而且经历也丰富,只是旁听生。平时都被刘克范安排做事。还有铁匠铺老板的儿子铁柱,以及药铺小学徒泽生。刘克范拆开信,眉头渐渐皱起:“修先生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了半年,如今国共合作,共产党在组织工农闹革命……” “革命”铁柱瞪圆了眼睛,“就是像洪秀全那样造反” 刘克范摇头:“不是造反,是要让咱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他压低声音,“信里还提到,有几位从广州、厦门回来的武平人,下月初要回县城活动。”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武所城。三天后,当修焕堂、李景森、钟磊三人背着行李出现在城关码头时,码头上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修焕堂穿着藏青中山装,眉眼间带着南方的温润;李景森身材高大,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藤箱;钟磊最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攥着本翻旧的《新青年》。 “这是修家大少爷!”有人认了出来,“听说在广州跟着孙中山先生的部下做事哩!” “还有李家二郎,听说在厦门念大学,学问大着呢!” 修焕堂微笑着拱手:“各位乡亲,我等此次回来,是想办几件实事——开夜校教百姓识字,办农会帮乡亲减租,再请个西医来给穷人看病。”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人群边缘的刘克范身上,“刘校长,明德学校能否借间教室,让我们办个读书会” 刘克范快步迎上去:“修少爷说哪里的话!学堂后院的空教室,随时能用!” 明德学校后院的空教室,很快成了武所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傍晚,十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庄稼汉、布庄学徒、药铺伙计便挤在八仙桌旁,听修焕堂讲“什么是阶级”,李景森讲“北伐军打到哪里了”,钟磊则掏出《新青年》念那些激昂的文字。 “各位兄弟,”修焕堂指着黑板上画的图表,“咱们武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地主收租七成,是军阀抽捐抽税,是穷人没地种、没书读!”他顿了顿,“可你们知道么在广州,农民自己组织了农会,把地主的田分给佃户;在汉口,工人成立了工会,和资本家谈判加薪!” 桂生坐在最前排,手里的铅笔在膝盖上画着圈。他是布庄的学徒,平日里最见不得东家刘克范的儿子刘富贵克扣工钱——上个月他替刘富贵跑腿买烟,多找了两文钱,反被骂“手脚不干净”。“先生,那咱武所也能办农会”他举手问道。 修焕堂点头:“当然能!但得有人带头。” 教室后排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铁匠铺的铁柱扯了扯桂生的衣角:“你听说没前儿个县警备队来搜查《曙汀》杂志,说是‘赤党刊物’!”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爹说,这些读书人怕是……” 话音未落,教室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黑制服的士兵闯进来:“谁是修焕堂有人举报你们聚众闹事!” 修焕堂神色不变,缓缓站起身:“军爷,我们不过是教乡亲们识字读书。”他转向刘克范,“刘校长,您作证,这教室可是学校的地方” 刘克范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道:“没错,这是明德学校的教室。修少爷他们办的是夜校,教百姓识字,为国储才。”他瞥了眼士兵腰间的驳壳枪,“军爷若不信,可去问县太爷——咱们武所城,总得有点开化的风气吧” 士兵盯着修焕堂看了半晌,最终哼了一声:“算你们走运!”转身带上门走了。 待脚步声远去,泽生才小声问:“先生,啥叫‘赤党’” 修焕堂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赤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他看向泽生,“就像你,每日在药铺做工,却连件新棉袄都穿不上——这样的日子,不该继续下去了。” 泽生的手攥紧了衣角。想想,药铺傅先生对自己是很好的。他想起了上个月帮刘富贵送礼时,看见王怀仁家的大宅院里摆着酒席,唱戏的班子唱了半宿,而自己的娘亲却在家煮着稀粥就咸菜。 桂生看着泽生笑了下,不知笑什么。 十二月的武所城,飘起了第一场雪。 刘克范邀了几个人到为灵洞山寺,说是赏雪。 寺庙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修焕堂、李景森、钟磊、刘克范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武平地图,上面标着地主、富商、警备队的位置。 “根据省委指示,”修焕堂郑重地说,“我们决定成立武平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他看向李景森,“李景森同志负责联络闽西各地的进步力量;钟磊同志负责组织工人运动,重点是城关的布庄、铁匠铺;克范校长……”他顿了顿,“你在武所城熟悉,学生多,负责联络农民和宣传工作,担任宣传委员。” 等会议开完。 刘克范征得修焕堂的同意,把外面放哨的桂生叫了进来。 桂生摘下帽子,抖落身上的雪:“修少爷,李少爷,我有个事要说。” 修焕堂欠欠相迎:“你坐。” 桂生坐下后,环顾四周:“我观察这些日子,修少爷你们办夜校、讲道理,确实是为百姓好。只是……”他压低声音,“县警备队队长陈虎和地主王怀仁走得近,最近盯得紧。我听说,他们怀疑你们是‘赤党’。” 李景森皱眉:“刘校长,您是明德学校的人,和他们接触多,能否帮我们打听打听” 刘克范说:“这是自然。不过……”他看向修焕堂,“桂生原来是药铺的学徒,人机灵,心眼正,对穷人的苦也看得明白。我观察他许久,觉得是个好苗子。” 修焕堂与李景森对视一眼,笑道:“刘校长推荐的人,我们自然信得过。” 三天后的夜里,桂生被悄悄叫到了明德学校的后院。刘克范等他坐下后:“桂生,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你个话——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们,为咱武所的老百姓做点事” 桂生捧着汤圆的手微微发抖:“刘校长,您说的是……” 修焕堂从里屋走出来:“桂生,我们想发展你入党。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党,你要愿意,就跟着我们一起干。” 桂生的眼眶红了。他想起了娘亲饿得直不起腰的样子,想起了刘富贵克扣工钱时的嘴脸,想起了夜校里修焕堂说的那些话。“我愿意!”他声音哽咽,“我愿意跟着你们,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李景森拿出一面小小的党旗——鲜红的底色上,黄色的锤子镰刀格外醒目:“桂生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队伍的一员了。等我们上报杭武党支部批准后再宣誓。” 窗外,雪依然在下,可济仁堂的后院里,却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 次年开春,武所城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城南的田野里,农民们开始翻地播种;城关的布庄里,学徒们悄悄传阅着《曙汀》杂志的抄件;明德学校的教室里,夜校的学生比往常多了三倍。 傅鉴飞的药铺成了情报中转站——泽生负责去各乡送药,顺便打听地主收租的情况;桂生在布庄留意富商的动向;铁柱则在铁匠铺打造农具时,偷偷给农会的骨干们多打几把锋利的锄头。 这天,修焕堂来到明德中学,和刘克范商量,让桂生带着几个中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去海丰参加农民运动,要把他们的经验做法学回来。在不久的将来武所也要成立农会。刘克范、修焕堂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南芝在边上看着也很是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