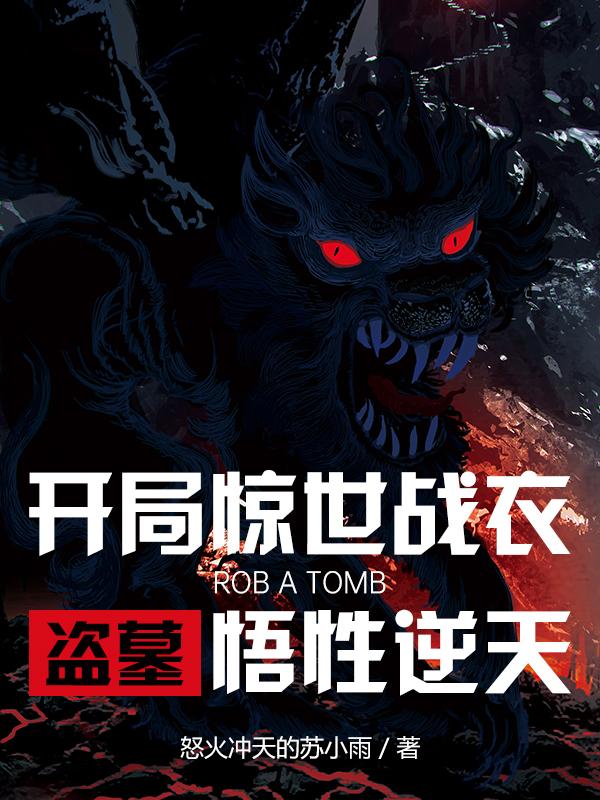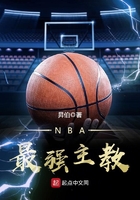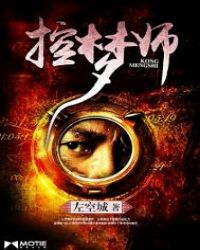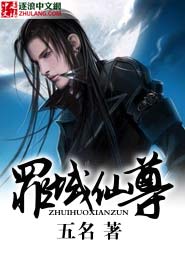第42章 诏中有刀,谁主沉浮
天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府门外,御林军的铜锣声震得门环嗡嗡作响。 苏清漪掀开车帘的手顿了顿,明黄色的伞盖在晨雾里格外刺目,伞下宦官捧着黄绢,蟒纹补子在风里翻卷——正是东宫大总管周福。 "苏姑娘,接旨吧。"周福尖着嗓子笑,眼角的皱纹里浸着阴鸷,"陛下口谕,陈默即刻领军北境,兵权归东宫监军使节制。" 苏清漪扶着车门下车,柳如烟紧随其后。 她的指尖刚触到黄绢,便觉那丝帛比寻常诏书薄了三分,入手带着潮意——像是连夜赶制的。 展开时,"敕"字的末钩在晨光里晃了晃,她瞳孔微缩:这钩画比内府印模偏左半分,玺印的朱砂色泽发暗,像是掺了旧年的矿渣。 "苏姑娘可是嫌圣旨烫"周福的笑声里带着刺,"难不成还想抗旨" 柳如烟的指尖掠过黄绢边缘,突然捏起一撮碎末。 她凑到鼻端轻嗅,檀木的腥气混着墨香钻进鼻腔——这是影阁典籍里记载的"仿诏膏",用檀香灰调陈墨,专用来伪造旧旨。 她不动声色地冲苏清漪摇头,袖中玉镯轻碰,发出两声短响。 苏清漪垂眸掩住眼底的冷意,将黄绢奉在胸前:"周公公辛苦,且到前厅用茶。"她转身时,衣摆扫过车门,瞥见陈默苍白的脸——他仍在昏睡,睫毛上凝着薄汗,像被暴雨打湿的蝶。 "阿烟,看住陈郎。"她低声道,将黄绢塞进柳如烟掌心,"我去取府库钥匙。" 柳如烟扶着陈默的肩将他抱下车,指尖触到他后颈的冷汗,心尖跟着颤了颤。 她抱着他穿过垂花门时,听见苏清漪的脚步声在青石路上敲出急鼓——那是苏清漪惯常的焦虑步速,只有当年宰相夫人病危时,她才这样跑过。 陈默被安置在暖阁的拔步床上,锦被下的身体轻得像片纸。 柳如烟守在榻前,望着他掌心的金纹随着呼吸明灭,忽然想起影阁古籍里的另一句话:"气运反噬印现,必有人谋乱于侧。"她攥紧黄绢,转身时撞翻了案上的茶盏,滚烫的水溅在腕间,疼得她倒抽冷气——这疼意倒好,能压一压心口的慌。 苏清漪冲进府库时,额角已沁出细汗。 她推开第三排檀木柜,取出一沓旧年公文,最上面的是三年前皇帝亲批的"赈灾敕令"。 比对之下,新诏的"敕"字钩画果然偏左,更让她汗毛倒竖的是——诏书用纸是"云鹤贡笺",这种纸三年前就因竹料短缺停产了,如今内府用的是"松纹笺"。 "好个东宫。"她将旧公文拍在案上,指节泛白,"连纸都舍不得用新的,倒急着要陈郎的命。" 后宅里,陈阿婆正蹲在廊下择菜。 见苏清漪过来,她颤巍巍扶着门框起身:"姑娘可是为那道诏" 苏清漪脚步一顿:"阿婆怎知" "昨夜扫院子时,听见檐角铜铃响得邪性。"陈阿婆的手摸向腰间的旧布包,"老奴当年在宫里当差,管过印泥库。 先帝遗诏的印,末钩要绕三绕,像团火苗。 如今这道诏......"她摇头,"连半团火都没有。" 话音未落,院外传来马蹄声。 柳如烟掀帘而入,袖中甩出半张焦黑的纸:"影阁的线人在东宫侧门捡的,是未烧尽的草稿。" 苏清漪接过,借着烛火辨认,"伪承嗣者,宜速除之"几个字刺得她眼睛生疼。 她转头看向柳如烟:"他们要除的,是陈郎" "不止。"柳如烟的声音像浸了冰,"陈郎的身世,怕是和先帝遗诏有关。" 正说着,李昭阳的声音从院外传来:"苏姑娘!"他掀帘时带起一阵风,将烛火吹得摇晃,"我刚收到消息,所谓的'监军使'是太子暗卫统领,今早带着三千御林军出了城!" 苏清漪攥紧那半张残纸,指节发出轻响:"假传圣旨,私调军权,太子这是要借北境战事做局。" "借刀杀人。"李昭阳一拳砸在案上,震得茶盏跳了两跳,"陈默若真上了北境,要么死在敌军手里,要么被监军使以'抗命'之名斩于军前!" 柳如烟望着榻上仍在昏睡的陈默,突然伸手按住他的手腕。 脉搏虽弱,却稳得像钟摆:"他在攒力气。"她抬头时,眼底闪过锐光,"等他醒了,这局,该翻过来了。" 暖阁外,日头爬到了屋檐角。 苏清漪将所有证据收进檀木匣,锁扣"咔嗒"一声,像给这场阴谋上了最后一道锁。 她转身看向陈默,他的睫毛突然动了动,像是要醒,却又沉入更深的昏睡里。 午后申时的风卷起窗纱,陈默的指尖在锦被下轻轻抽搐。 榻前三人的对话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他听见苏清漪说"诏书是假的",柳如烟说"东宫要除你",李昭阳说"他们要你的命"。 他想睁眼,却觉得眼皮重逾千钧。 意识深处,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今日签到已触发......" 但更清晰的,是胸腔里翻涌的热意——那是被反噬的气运在灼烧,也是即将破土的锋芒在攒劲。 午后的日头斜斜切进窗棂,在檀木案几上投下半片金斑。 陈默睫毛颤了三颤,终于在暖阁的熏香里缓缓睁眼。 "陈郎!"苏清漪正攥着帕子替他拭额角冷汗,见他醒转,帕子"啪"地掉在锦被上。 她俯身时鬓间玉簪晃动,碎玉声里裹着哭腔,"你可算醒了。" 柳如烟倚在妆台前,指尖还捏着半块未烧尽的诏纸。 听见动静,她旋身过来,腕间银铃轻响:"醒得正好,东宫的假诏还在府里供着呢。" 陈默望着三人紧绷的眉眼,喉间泛起一丝腥甜。 他记得昨夜为镇压气运反噬,强行运转《九阴真经》到第七重,内息在奇经八脉里撞得七荤八素。 此刻虽浑身乏力,意识却异常清明——系统的提示音还在识海回响:"今日签到触发成功,获得《兵符御令术进阶篇》。" "先说重点。"他撑起身子,苏清漪忙扶他靠在软枕上。 李昭阳从门外大步跨进来,腰间佩刀撞在门框上,"当啷"一声:"太子派了暗卫统领当监军,带着三千御林军往城北大营去了! 那假诏说你抗旨就斩,打输了也是死——" "他不怕我打不赢。"陈默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寒刃出鞘的锐意,"他怕我打赢了。" 三人皆是一怔。 柳如烟眯起眼,指尖摩挲着袖中影阁密报:"陈郎是说......" "北境二十万边军,缺的从来不是兵力。"陈默垂眸望着掌心淡金纹路,那是系统签到三年觉醒的"气运纹","缺的是能把散沙捏成剑的人。 若我真能带兵破敌,军功加身,再加上我这'潜龙命格'......"他抬眼时眸中寒芒乍现,"太子的储位还坐得稳么" 苏清漪突然攥紧他的手腕。 她的手凉得像浸了冰,却比任何言语都滚烫:"那道假诏用的是旧纸旧墨,连印泥都掺了水。 我们有证据——" "证据"陈默摇头,"太子要的是我死在北境,死无对证。 就算你拿着证据闯宫,陛下若装糊涂......"他没说完,苏清漪的指甲已掐进掌心,在绢帕上洇出小红点。 "所以得让他们的局,反过来咬自己。"柳如烟突然插话。 她从袖中抖出个青铜小铃,铃身刻着云雷纹,"影阁藏着先帝当年私用的验诏铃,用承嗣血激活,能辨诏旨真伪。" 陈默接过铜铃,指腹擦过铃身斑驳的绿锈。 系统提示适时响起:【检测到"先帝验诏铃",触发隐藏签到条件,获得"兵符御令术气机共鸣"】他瞳孔微缩,突然闭目。 内息顺着《兵符御令术》的脉络流转,刹那间,京城内外的军令气机如星子般在识海亮起。 他"看"到一道乌沉沉的气线从东宫穿出,像条毒蛇缠向城北大营——那是太子试图用伪诏覆盖他昨日刚从陛下手里接过的虎符气机! "果然动手了。"他睁开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柳姑娘,这铃借我。 苏姑娘,取我昨日得的虎符。 李将军......"他看向李昭阳,"随我去大营。" 黄昏的营门在夕阳里镀了层血光。 监军使周立站在点将台中央,手里举着明黄诏书,声音像破锣:"陈默抗旨不遵,着即夺其兵权——" "且慢。"陈默的声音清清淡淡,却像根细针戳破了喧嚣。 他踩着满地残阳走上高台,腰间虎符在风里晃出冷光。 周立的脸瞬间煞白——这赘婿昨日还病得下不了床,此刻竟直挺挺站在这里,眼尾泛红,倒像头刚醒的恶狼。 "周大人说这是圣旨"陈默将青铜铃悬在案上,指尖咬破,血珠"啪"地溅在铃口。 铃身突然震颤,发出清越龙吟。 他展开虎符,运起"兵符御令术",刹那间,全场将士腰间的军令牌同时鸣响,声浪撞得旗幡猎猎作响! 周立手里的诏书"唰"地掉在地上。 众人望去,那朱红的玺印正在褪色,像被水浸过的墨迹,渐渐露出底下一行小字:"太子令,斩陈默以绝后患"。 "伪诏!"有人喊了一嗓子。 点将台下瞬间炸开,刀枪出鞘声连成一片。 周立踉跄后退,撞翻了案上的酒坛,琥珀色的酒液溅在伪诏上,将"太子"二字泡得愈发清晰。 "末将愿随陈将军出征!"左先锋将率先单膝跪地,铠甲撞在青石板上,"虎符共鸣,此乃天示!" "愿随陈将军!" 声浪掀翻了营门的旌旗。 陈默望着台下跪成一片的将士,指尖轻轻抚过虎符。 系统提示在识海响起:【兵符御令术气机共鸣激活成功,当前可操控五万以下军令】他垂眸时,恰好看见苏清漪站在营门外,被夕阳拉得很长的影子里,攥着那方染血的绢帕。 夜幕降临时,校场点起了千百盏火把。 李昭阳拍着陈默的肩,酒气裹着豪情:"陈兄弟,明日北境见真章!"他话音未落,柳如烟的马车已"吱呀"停在台下。 她掀帘递出一张拓片,墨香里浸着土腥气:"影阁最后据点被毁前,线人挖出块石碑。" 陈默接过拓片,"乾元承嗣,当继紫宸"八个字在火光里泛着冷光。 他指尖微颤,突然想起陈阿婆昨日说的"潜龙命格",想起苏清漪比对诏书时发白的指节,想起系统签到千日时解锁的"武圣战魂"...... "真正的战场不在北境。"他转身对苏清漪低语,"在宫墙之内。" 苏清漪望着他眼底翻涌的暗潮,突然伸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 她的手还是凉的,却带着从未有过的温度:"我信你。" 归途中,马车碾过满地碎琼似的月光。 陈默闭目养神,系统提示悄然浮现:【连签第1002日,解锁"真龙护心诀第二重"——可短暂屏蔽帝王望气术窥探】他攥紧拓片,指腹压过"承嗣"二字,像是要将这两个字刻进骨血里。 北境的风雪,已在千里外翻涌。 当陈默率三千锐卒行至雁门关外三十里时,断脊谷的风卷着雪粒劈头盖脸砸下来。 他勒住马,望着谷口那座斑驳的石碑——上面隐约可见"埋骨处"三个大字。 "将军,前面就是断脊谷。"斥候策马回报,"谷里风大,夜宿恐有险情。" 陈默抬头望向阴云密布的天空。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这次却混着极淡的龙吟:【检测到"断脊谷"为上古战场遗迹,触发隐藏签到条件......】 他笑了,拍马向前。 风雪里,三千铠甲映出冷光,像一条银色的龙,缓缓游进了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