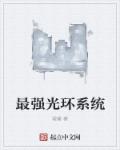第418章 市井听风
奉先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阿里小说网novels.allcdn.vip),接着再看更方便。
洛阳城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与逐步恢复,虽尚未重现昔日帝都的全盛气象,却也已一扫董卓强行迁都后留下的破败与萧条。主要街道被重新平整夯实,坊市之间人流日渐稠密,尤其在新近规划辟出的商贸区域,更是车马络绎,驼铃与叫卖声此起彼伏,显露出顽强的生机。 “吕氏暖锅”的洛阳总店,便雄踞于此间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侧。三层木制楼宇,飞檐斗拱,气势不凡,门前悬挂着巨大的黑底鎏金招牌,在春日温煦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老远便能吸引行人的目光。此刻还未到午间正式开市的时辰,店门口已然有十余人排队等候,店内飘散出的、混合着浓郁骨汤醇香与十几种辛香调料独特气息的诱人味道,远远便能闻到,如同无形的钩子,牢牢勾住往来行人的脚步与食欲。 李肃今日穿着一身质地考究但样式颇为普通的暗纹锦袍,腰间束着玉带,手中把玩着一枚温润的玉佩,看上去就像个家资殷实、闲来无事四处溜达的富家翁。他背着手,步履从容地踱进店内。跑堂的小二眼尖,显然早已认得这位不常露面却地位尊崇的东家,脸上立刻堆起热情洋溢却又丝毫不显谄媚的熟练笑容,快步迎上,将他恭敬地引至三楼一处最为僻静、且能俯瞰大半条街景的雅间。 “东家,您来了。”早已候在室内的掌柜,是个年约四十、面容精干、眼神活络的中年人,见李肃进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躬身行礼,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 “嗯,闲来无事,顺路过来瞧瞧。”李肃随意地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自顾自地踱步到那扇临街的支摘窗前,伸手推开半扇,目光仿佛漫不经心地扫过楼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景,“近来生意如何” “托东家的洪福,生意极好,可谓日进斗金。”掌柜的赔着笑,手脚麻利地用上好的瓷杯为李肃斟上一杯滚烫的香茗,“尤其是这开春时节,天气反复,乍暖还寒,来吃暖锅驱寒暖身的客人最多,常常是一座难求。昨日的流水明细与各处开销账簿,小人已整理好,就放在那边案上了,请东家过目。”他边说,边指了指房间内侧那张沉稳的紫檀木书案。 李肃踱步过去,并未立刻伸手翻看那摞账本,而是先拿起了旁边一本看似记录“各地客官风味偏好杂录”的线装册子,慢悠悠地一页页翻看着。上面用极其细密工整的字迹记录着诸如:某月某日,三位来自蜀地的客商,偏好重麻重辣,特意要求后厨多加花椒与茱萸;某月某日,几位自称从颍川游学而来的士子,嫌汤底口味过咸,言及家乡饮食清淡;某月某日,一队河北来的行商,对店中特制的蒜泥豆豉酱料赞不绝口,临走时还特意询问可否高价购买一些带走…… “嗯,天南地北,客人口味各异,众口难调。后厨那边要更灵活机变些,可根据客人的大致来源地,酌情调整汤底咸淡与蘸料搭配。”李肃像是纯粹在点评生意经,随口吩咐着,“尤其是那些从邺城、许都这等大地方来的客人,见多识广,口味或许更刁钻些,务必要伺候得更加周到细致,让他们不仅吃得满意,更要记住咱们洛阳‘吕氏暖锅’这份独一无二的滋味。” 掌柜的心领神会,凑近半步,声音压低了些,带着几分秘闻的意味:“东家放心,小人省得,早已再三叮嘱过伙计们。说起来,前几日,确有一队规模不小的商贾,持的是冀州路引,听口音是邺城那边来的,包下了二楼最大的雅间,在店里连吃了三日,对我们这暖锅是赞不绝口。席间听他们偶尔交谈,除了夸赞锅子美味,倒也夹杂着不少抱怨之词。” “哦”李肃端起茶杯,轻轻吹着水面漂浮的茶沫,眼皮都未抬,仿佛只是随口一问,“都抱怨些什么” “多是一些行商路途上的琐碎事。”掌柜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如同耳语,“说什么如今河北地界,官盐价格虽然表面稳定,但品质大不如前,苦涩难咽,而品质好些的私盐价格又高得离谱,让他们这些行脚商人利润薄了不少,生意越发难做。还隐约提到……邺城大将军府那边,似乎在严查各路往来商队,赋税名目增多,尤其是针对往并州、司隶方向的商队,盘查得格外严厉,盘剥得也狠,下面怨声载道,只是敢怒不敢言。” 李肃抿了口清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不置可否。掌柜的善于察言观色,见状继续低声禀报:“还有……小人平日留意往来许都方向的客商闲谈,听说那边市面上,咱们的‘玉皂’几乎已经绝迹,偶尔在黑市上出现一小块,价格都贵得吓人,简直成了大户人家女眷之间相互炫耀的稀罕物。倒是许都官营的作坊新推出了一种皂,价格低廉许多,但据说……去污效果远远不及咱们的‘玉皂’,而且用后皮肤干涩紧绷,颇受诟病。” “嗯。”李肃放下茶杯,手指在那本“风味杂录”册子上轻轻敲了敲,发出笃笃的轻响,“客人的喜好、挑剔乃至抱怨,都是咱们改进经营、揣摩人心的明镜。这些林林总总,无论巨细,都要仔细记下,定期汇总。” “是,是,东家教诲的是,小人明白,一直安排专人负责记录整理。”掌柜的连连点头,态度恭谨。 李肃又在店内慢悠悠地转了一圈,信步去后厨看了看备料的新鲜程度,随口问了问几位老伙计的近况,甚至还尝了尝今日新熬的汤底,这才仿佛心满意足,脸上重新挂起那副富家翁的闲适笑容,背着手,慢悠悠地离开了暖锅店,身影很快便融入门外喧嚣涌动的人流之中,不见踪迹。 然而,他并未走远,也未返回自己在城中的宅邸,而是不动声色地拐进了相隔两条街巷的一处门面普通、招牌陈旧的山货栈。这货栈表面看来与城中其他经营土产批发的铺面无异,但穿过前堂,进入后院,却是别有洞天。一间门窗皆用厚毡遮蔽、内外隔绝的密室内,炭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苗驱散了室内的潮湿与阴冷,也映照出李肃脸上那已然彻底褪去的闲适之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鹰隼审视猎物般的锐利与冷静。 他在这间只有极少数心腹才知道的密室里坐下,面前的书案上,早已铺开了方才在暖锅店看似随意听闻的、以及近期通过隐秘渠道从长安、晋阳等其他分店送来的各类“市井见闻”与“风味反馈”。这些信息庞杂琐碎,如同散落一地的珍珠。 李肃目光如炬,迅速浏览筛选。他拿起一支吸饱了墨的细狼毫笔,取过几张特意裁剪过的、质地坚韧的桑皮纸,开始快速书写。他使用的并非寻常文字,而是一套内部约定、外人绝难理解的简略符号、数字与特定代称,确保即使密信落入他人之手,一时半刻也难以解读。 笔尖在纸面沙沙移动,留下简洁却信息量巨大的记录: “邺线:盐政紧缩,官盐质劣价隐涨,商路阻滞迹象显,底层商贾怨气积累。需重点核查其针对并州、司隶方向商路之具体管控措施与强度。” “许线:皂类利润空间依然巨大,官营替代品品质低劣,未能满足需求,私市渴求程度高。可考虑……经由第三方渠道,极少量、分批放货,进一步抬升价格,试探其市场反应与官方容忍底线。” “荆线:江夏战事仍处胶着,往来商旅趋于谨慎,沿线粮价已有小幅波动。综合各方信息,黄祖用兵保守,似仍未调动其麾下侧翼某股非嫡系力量(代指甘宁部),此或可加以利用。” 他写得极快,条理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判断都基于多条信息的交叉印证。哪些是无关痛痒的市井闲谈,哪些可能折射出对手势力内部的治理困境与矛盾,哪些又蕴含着可供利用、加以放大或制造事端的机会点,在他心中自有一架精准的天平进行衡量。 写罢,他将几张桑皮纸分别卷成细小的纸卷,小心翼翼地塞入几个看似普通、用于装药材的细竹管内,用特制的火漆仔细封好接口,并在火漆上留下一个微不可察的印记。他伸手,在旁边一个不起眼的铜铃上轻轻敲击了两下,发出清脆而短促的声响。 几乎是立刻,一名穿着货栈伙计普通棉布服饰、但眼神异常沉静精悍的年轻人,如同影子般悄无声息地推门走进来,垂手侍立。 “即刻发出,按甲字三号紧急路线传递,务必亲手送至长安,面呈贾公,不得有误。”李肃将几个竹管递过去,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是。”年轻人接过竹管,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与询问,只是重重点头,随即转身,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融入密室的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 密室内重归寂静,只有炭盆中偶尔爆出的噼啪轻响。李肃独自坐在案前,身体微微后靠,手指无意识地、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桌面,目光沉静地望向虚空,仿佛在穿透墙壁,审视着远方那些波谲云诡的局势。暖锅那独特的、令人垂涎的香气仿佛还隐隐萦绕在鼻尖,但此刻,那市井的喧嚣与烟火气已然远去,被隔绝在这间密实的斗室之外。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笑容可掬、和气生财的店铺东家,而是吕布麾下,一张正不断编织、扩展的无形情报大网的关键枢纽之一。这些从杯盏交错间、从商旅抱怨中、从市井流言里收集来的微风,正被他这只无形的手汇聚、提炼,化作一枚枚无声的信使,沿着隐秘的通道,飞向长安,成为那个庞大战争机器与政治棋局在决策时,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往往能影响天平倾斜的、不可或缺的依据。
![[综]穿越成各种奇葩角色](https://img.picturecdn.com/images/146411/5af61ece26cec1d414ca5cdd6d1f8aef.jpg)